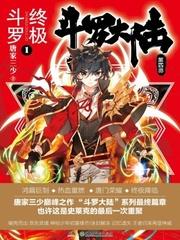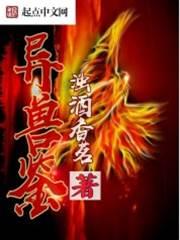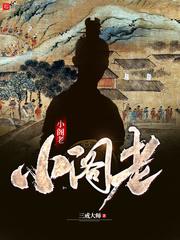18 (18)
兩地是突厥和薛延陀兩國南下的要道。
“敵人已占領這幾處戰略要道,随時都有可能從這幾個要塞直沖幽州地帶!”
衆人紛紛上前,聚在一起,觀察戰略形式。
大家都已從前方了解了三國聯軍大致的動向,他們都清楚,雖然敵軍尚未正式宣戰,但都已提前動員,占住了戰略要道。
但大家所了解的情報并不如長孫無忌這般齊整,并不了解北方戰勢有如此緊迫。
現如今,長孫無忌将這幾處戰略要道标了出來,讓衆人看清敵軍的動向。
衆人一看登時便心驚膽戰,照這地圖上所标,敵軍已繞過燕山屏障,将幽州地區團團包圍住了。
一旦失去燕山屏障,那幽州附近大片開闊平坦的地區,就完全暴露在敵軍的騎兵鐵蹄之下。
突厥和薛延陀都已騎兵為主,草原鐵騎名聲在外,他們若是同時對幽州發起進攻,那幽州是必丢無疑。
幽州一丢,敵軍再以幽州為據,盡遣鐵騎肆虐黃河以北,唐軍勢不能敵!
正當大家心生驚懼時,長孫無忌再接再厲,又繼續道:“這突厥和薛延陀的鐵騎勢如猛虎,高句麗也絕非良善之輩!”
“想當年,前隋三征高句麗,哪一次能在高句麗手中占得便宜了?”
長孫無忌聲聲震耳,又将大家心中有關高句麗的悲慘記憶都引了出來。
081 救援良策
二十年前,隋朝曾三次東征高句麗,幾乎耗盡了隋朝的錢財兵馬,但這三次東征,全都告敗。
在這三次東征中,漢人死傷無數。尤其在第二次東征中,薩水之戰有十幾萬漢人被砍了頭,人頭聚攏,堆成了駭人的京觀。
這三次東征高句麗,耗盡了大隋的氣數,可以說是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。
如今唐朝已立,但距離東征高句麗時間并不久遠,大家都能記得高句麗給漢人帶來的苦難。
尤其是東北一帶的唐人,稱一句“患高句麗更甚猛虎”,這一點都不為過。
在場諸将聽見長孫無忌提起前隋三征高句麗,皆是心有戚戚。
尤其是秦瓊,他當年曾在前隋來護兒帳下,親自參與過東征之戰,如今再回憶起來,更是不禁唏噓感嘆。
“高句麗,實乃強敵也!”
衆人一陣唏噓,長孫無忌更顯得意,他将地圖一收,蓋棺定論道:“這黃河以北,眼下已無險可守,若是誰強行過河,想要與北方三國硬拼,絕對是死路一條!”
方才大家還有心氣與長孫無忌頂嘴,但經過被他這一番分析,衆人皆是凝眉怔忡,默然不語。
李世民也被震得大為驚駭,照這情勢分析,黃河以北是萬難守住了。
他心下一嘆,若是恪兒前往北方參戰,定要勸他不能過河,否則便是九死一生。
長孫無忌這一番說辭,讓場中氣氛有些凝滞,大家這會兒都冷靜下來,細細分析如何破敵。
正在這時,那守在李世民身邊的王德突然身子一晃,向殿外瞧去。
他随即在李世民耳邊說了兩句,經李世民點頭後,便又朝殿外走去。
衆人正自好奇,卻見那王德出了甘露殿,很快又轉了回來。
但他這次回來,手中多了一份書信。
王德拿着那封書信,恭恭敬敬地走到李世民身邊,低聲道:“這是蜀王經暗衛送上來的信!”
李世民心中疑惑,不知道李恪又有何部署,眼下情勢危急,他便當着衆人的面,打開了那封書信。
這時,場中諸臣還是一頭霧水,他們不敢造次,只能等李世民看完書信再行商議。
卻見李世民這時臉色已迅速轉喜,到最後将那書信一展,振聲道:“恪兒又送來的一封書信,諸卿傳閱一番!”
王德很快将那書信接過,而後遞給了殿中的大臣,大家紛紛傳閱。
這封書信分為兩部分,前一部分,是李恪所書,有關幽州救援的計劃。
只一看到開頭,大家便是一驚。
這幽州之事,他們身在長安,都是近日通過各方打聽,才了解到的。
可李恪,身在蜀地,他又是如何得知幽州之事的?
更讓人吃驚的是,李恪不但了解幽州情況,他還能迅速作出反應,制定了解決幽州困境的辦法。
依李恪所言,他蜀地有一商會,可以提供錢糧,讓當地官府出面,組織幽州百姓遷往川蜀之地。
他雖說得含蓄,但即便是關隴集團的官員也能猜出,這所謂的商會,正是李恪名下的蜀國商會。
但這商會并非白白出錢,李恪言明,打完仗之後,商會會與幽州官府合作,重建幽州。只是戰後十年,幽州所産錢糧,扣除佃農的基本生活保障,其餘盡歸商會所有。
但考慮到土地的所有權是那些幽州本地的士紳地主,若拿走全部收益,他們一定無法接受。所以,李恪視這些地主為商會投資者,分六成收益給這些士紳地主。
看完李恪所提的解救幽州的辦法,衆人皆覺得這主意不錯。
幽州之難,首當其沖的就是缺糧食,只要能提供糧食,暫時解決百姓饑荒問題,那還有得救。
解決饑荒之後,就要想辦法解決百姓的存留問題,畢竟即将要打仗,百姓留在那裏,生産生活都成了困難。總不能一直讓軍隊保護着,國家出錢養着吧?
但李恪所提,将百姓轉移到蜀地,便能将戰争的影響降到最低。百姓不再受戰争所擾,也能安心生産,在蜀地同樣生存下去。
而對于商會來說,雖然前期提供錢糧,但戰後十年的收益,絕對遠超商會所供應的錢糧,只要這場仗能順利守住幽州,這是筆大賺特賺的生意。
蜀王黨衆人紛紛點頭答應,商會掙錢,就是他們掙錢,他們豈有不答應的道理?
既能解救幽州百姓,又能順道掙錢,于名于利都有得賺,不答應才怪呢!
便是長孫無忌等關隴集團的官員,見此提議也紛紛眼紅,更有甚者,還要考慮如何加入李恪的計劃,也出錢參與其中。
“不錯!蜀王這主意好!将那些百姓轉移到安全地帶,往後打起仗來,也輕松得多!”
李績點頭稱贊。
房玄齡也幽幽笑道:“于國于民,皆有利處,蜀王這法子能行!”
大家誇得還比較含蓄,唯獨程咬金這時跳出來,大笑道:“蜀王殿下這法子好,既解了圍,還能順道掙錢!這生意絕對不虧!”
說完,他又是哈哈大笑,這引得周邊商會成員紛紛抛出白眼。
大家心知肚明的事,你非得說破,這不是讓李世民和關隴集團的人看笑話麽!
李世民沒有理會程咬金等人,他這時正在思考,李恪提出這個解決方案,是否有更深一層的涵義。
士紳、土地,這兩者結合到一起,不得不讓李世民多想。
他不由得回想起,當初在與楊妃一起吃飯時,李恪曾提出,他以後要想法子從士紳手中收走土地。
這樣看來,李恪是打上了幽州士紳土地的主意了。
十年收成,全都歸商會所有,士紳作為投資者,能拿六成……
他心中突然一敞亮,這不就等于,李恪用土地的六成收益,從士紳手中拿走了土地嗎?
十年之後,只要士紳能賺到不輸于從前的利益,難道他們還要退出投資嗎?
淡淡笑了笑,李世民不禁自嘆道:“恪兒,朕當初還念你所說的妄言絕不可能實現,沒想到,你真有此等好手段,能将士紳手中的田地弄到自己手中。”
082 以身犯險
杜如晦這時感嘆:“确實是妙!”
他又回頭看向房玄齡,笑道:“房兄,你我同為宰輔之臣,號稱謀臣相才,怎麽就想不出這等精妙的主意呢?”
這房謀杜斷,號稱李世民的治下謀臣之最,卻沒能敵過一個尚未及冠的皇子。杜如晦這番自嘲也不無道理。
房玄齡搖頭感嘆:“蜀王之才,豈是我等能及?他若為相,定是治世能臣!”
房玄齡不無感嘆,李恪這主意的确算得上是萬全之策。
這一來解救了百姓饑荒問題,二來又解決了戰争的後顧之憂,三來又能掙得錢財土地。
這般面面俱到的思慮謀劃,當真非世人能及。
以前只道蜀王謀略武力皆非常人,如今看來,其對治國之道,也極其擅長精通,實在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全才通才!
待房、杜二人說完,蜀王黨衆人紛紛拱手,齊齊向李世民贊道:“恭喜陛下,得此麒麟皇子,文武雙全之才,日後定能輔助聖上,保我大唐山河永固,太平康樂!”
自己的兒子被這麽一通誇贊,李世民也難得得意起來。
這時,卻聽長孫無忌開口打斷:“衆人皆誇贊蜀王解救幽州之道,某倒是認為,蜀王所提的第二部分,倒是極富勇武謀略,若依他所言,定能解決北方困境!”
長孫無忌誇贊李恪,這倒是奇事。
在場衆人都已看過書信,自然知道李恪書信中的第二部分,正是破敵之策。
李恪在信中言明,他要揮軍北上,直取高句麗。
這高句麗,是北方三雄中,兵力最強的一個。其麾下有三十多萬人馬,遠多于突厥和薛延陀。
照李恪的說法,高句麗一滅,其他兩國便再也不敢妄自動手,這聯軍不攻自破。
高句麗雖然兵強馬壯,但其也有軟肋,就是鴨綠江。
從高句麗揮兵南下,進攻大唐,必須要跨國鴨綠江。
但前隋三次東征,高句麗也并非毫發無損,當時打得也十分慘烈。據李恪所言,高句麗的船隊,都已在前隋東征時,被盡數殲滅,直到現在還未重建。
這就給高句麗南下征戰帶來了隐患。
大軍攻伐,必須要有糧草後援,但高句麗的船隊未能重建,運送糧草就成了問題。
現如今,高句麗的糧草,都是通過跨江大橋運過鴨綠江的。
而李恪打算盯準這點,直切高句麗的運糧路線。
他準備等高句麗大軍跨過鴨綠江,再占據鴨綠江畔的安市城。
那安市城乃是連接鴨綠江的重要節點城市,跨江大橋正是在這座城市修建的。
一旦占據安市城,敵軍的糧草就運不到南方,大軍一定會立刻斷糧。
眼下正是冬季,高句麗大軍一旦斷糧,很快就會喪失戰鬥力,最終,他們會餓死在鴨綠江畔。
這一招,可謂精準至極,直接掐住高句麗的脖子,活活将其餓死。
而一旦高句麗戰敗,那突厥和薛延陀,兩個只會打順風仗的游牧民族,壓根就成不了氣候。
長孫無忌這時誇贊李恪,讓衆人不免奇怪。
誠然,李恪的戰術謀略,讓人無不佩服,但蜀王黨這些人誇耀倒還好理解,長孫無忌這李恪的死對頭,怎麽會誇贊他呢?
不理解歸不理解,但任誰看了李恪的戰略規劃,都會在心中贊嘆這策略實在精妙。
掐住糧草後援,守住鴨綠江,将高句麗大軍餓死在家門口。
這一步若能順利達成,那高句麗必然戰敗,北方三國的聯軍也随之土崩瓦解。
秦瓊唏噓道:“此戰法深合我意,蜀王殿下果然用兵如神,為将帥之才!”
大家紛紛點頭同意,心道蜀王文治武功,皆為當世之冠,實乃舉世無雙之大才。
但杜如晦卻沒有附和,他一反衆人,蹙眉道:“秦将軍是身先士卒的猛将,此法自然合你心意。可是,你可曾想過,蜀王何等身份?他這樣做,簡直是将自己放進了敵人的刀鋒鐵騎之下。那高句麗大軍一旦醒悟過來,狂攻安市城,何其兇險?”
秦瓊乃是沙場上的急先鋒,哪裏有危險就沖向哪裏,他之所以對此計心有向往,正是因為這計謀之奇險詭谲。
深入敵軍後方,掐斷糧草要道,這計謀說起來精妙,但其實要點就是一個“險”字。
一般人,能做出這種深入敵軍後方,把自己置于險地的行徑來嗎?
想清楚這點,秦瓊苦笑着嘆息,他自己沖鋒陷陣慣了,差點忘記李恪乃是國之希望未來,做這等危險之事,實在不太明智。
而杜如晦點破此點,雖然話鋒指向的是秦瓊,其實暗地罵的是長孫無忌。
衆人這才明白,長孫無忌之所以會誇贊李恪的戰術謀略,其實就是慫恿李世民答應這戰法,将李恪送到鴨綠江畔。
這種主動将自己送入思路的戰術,長孫無忌怎麽會不支持呢?
眼下,李世民也從杜如晦的話裏,聽出了這戰術的兇險,他心中也在猶豫。
李恪的戰術一旦成功,便能瞬間瓦解三國攻勢,成功扳回北方戰局。
可……萬一失敗呢?
李恪可是他現在最為仰仗的人才,一旦戰死在鴨綠江畔,那大唐還有誰能抵擋三國聯軍?
便是不談戰略,那可是自己的皇子,他怎能願意看自己兒子身陷死地呢?
李世民陷入兩難。
“陛下,蜀王此計精妙無雙,如依他所設計,一定能順利将三國聯軍擊潰。如此戰法,請陛下一定采納!”
長孫無忌這時又鼓勁道。
他一開口,關隴集團的官員也紛紛跟進。
“望陛下采納蜀王謀略,擊敗聯軍,保我大唐河山!”
“望陛下為我大唐山河社稷着想,采納蜀王戰法!”
這些關隴集團的人巴不得看李恪送死,紛紛進言,要李世民采納李恪的建議,放他深入鴨綠江,攻擊敵方腹地。
李世民此刻天人交戰,心中糾結不已。
他不斷思索着,是否還有更好的辦法,能取代這個危險的打法。
可敵軍緊逼在前,若不出此奇詭招數,如何能解決當前困境?
083 進軍北上
對于李世民來說,現在有兩條路可選。
若保李恪安全,他便只能放棄黃河以北的大片領土,讓李恪鎮守黃河沿岸,抵擋敵軍。
但若為了保住大唐山河,他只能忍痛答應李恪,放他身陷險地。
此刻蜀王黨衆人也都沉默了,他們不想打擾李世民的思緒,将選擇權交給聖上。
雖然大家都不想李恪以身犯險,但這是他自己的主意,衆人也不好反對。
畢竟李恪的勇武,衆人是看在眼裏的,大家也隐隐相信,李恪的計謀能順利實施,能将三國聯軍擊敗。
李世民猶豫良久,最終重重的嘆息一聲:“既然恪兒出此險招,想來是有必勝的把握。朕……應允了!”
他立即吩咐暗衛,快馬加鞭給李恪送信,詢問他還需朝廷提供什麽幫助。
此刻的李恪仍在蜀地備戰,自從收到北方三國準備攻擊大唐的消息,他便開始調撥糧草兵械,動員手下将士準備北上。
他已組建一只全騾馬化的軍隊,這支軍隊行軍時由戰車拉動,保證極高的機動性。
這種戰車是李恪親自設計的,一共有兩節,前後節各有兩個車輪,由牛或馬牽引,一次能拉動十五人,或拉載十人外加全部補給。
這種戰車能運載七萬精銳步兵,這些步兵都經過精挑細選,具備較高的作戰能力。
除此之外,這一仗,他還打算帶上五萬騎兵,十三萬步兵,加起來一共二十五萬之衆。
這麽大規模的部隊,要想運送至東北地區,動靜不小,但擺在李恪面前的最大難題,是糧草辎重的運輸問題。
安市城距離極遠,而且深處敵方腹地,要想通過深入敵軍後方,将糧草運輸到那裏,顯然不太容易。
萬一在那裏與高句麗發生持久戰,糧草不足的問題,将會給他造成很大的麻煩。
李恪一直在尋求解決糧草運輸問題的辦法,眼下只有陸路和水路兩種方案。
走陸路是常規辦法,但這樣的話,一旦敵人掐死鴨綠江,那等于掐死了他的運輸線。
而且敵軍馬上就要跨國鴨綠江,進入到東北地區,一旦他們占領東北地區,那糧草能否通過東北,運送至安市城,也是個問題。
所以,李恪還想從水上開辟一條運糧通道,他已構思,從山東地區入海,一路沿海岸線北上,直接送到安市城。
但這樣做,需要大量運輸船舶,李恪手頭上還沒有這麽多船。
正當他為此事撓頭的時候,李世民的書信送到了。
一看李世民詢問他有何要求,李恪當機立斷,向朝廷索要戰船。
他向朝廷索要山東沿海的三萬艘戰船,用以運輸糧草辎重。
既然李世民已然同意他的打法,那李恪也不再猶豫,發完書信,他即刻整理部隊,準備出發。
天還未亮,成都城外已聚滿百姓,将整個城門兩側擠得滿滿當當。
人雖然很多,但此刻城外卻保持着安靜,大家都齊齊噤聲,目光緊盯着城門口的方向。
前方的人群有些騷動,這騷動不斷自城內向城外蔓延。
漸漸地,衆人已能看到,有一支大部隊自城內向城外而來。
待那支部隊走近,衆人已能看清,走在最前方的,是一騎白馬,馬上坐着的,正是蜀地的領主,李恪。
李恪一身亮金盔甲,身後兜着随風飄揚的紅袍,他身騎白馬,神情堅毅地領兵前行,儀态英武不凡。
在他身後,是威風凜凜的五萬騎兵部隊,個個精神抖擻,英氣逼人。
再往後,在衆人看不清楚的地方,是七萬乘坐戰車的精銳步兵及十三萬普通步兵。
這是李恪發兵出城的日子,全城百姓全都齊聚城門口,送李恪出城。
部隊行至城門口,李恪單手一擡,衆将士齊齊止步,停了下來。
李恪再一打馬,悠悠行至城門口,此刻,所有百姓的目光全都齊聚在他一人身上。
此刻晨風吹氣,卷起李恪身後紅袍,襯得他潇灑不羁,飄逸出塵。
“成都城的百姓們!”
李恪用盡氣力,振聲呼喊着,希望能讓更多人聽見自己的聲音。
“我,李恪,當今聖上第三子,蜀地之王……”
“今日領兵出城,前往北方,解救北方百姓,誅殺犯我山河的異族敵寇!”
他的話一說完,成都城內外的百姓齊齊鼓掌,衆人無不振奮激昂。
“一定要将那些犯我大唐的賊人通通殺光!”
“蜀王一定要平安歸來,再領我成都百姓發家致富!”
“犯我大唐者,殺!!”
百姓們紛紛吶喊助威,盡情揮灑着胸中激情。
待衆人掌聲吶喊聲漸漸停息,李恪繼續開口。
“這一次出戰北方,我蜀地兒郎支援北方,為大唐奉獻熱血,盡力拼搏!他們是我們蜀地百姓的驕傲,是我李恪的驕傲!”
“我李恪,為治下能有如此多慷慨豪邁、英勇無畏的将士而自豪!”
這話一出,衆百姓再度齊聲鼓掌,大家紛紛為将士們吶喊歡呼,鼓勵衆将士英勇殺敵,驅逐賊虜。
待衆人掌聲稍停,李恪又打馬回身,面向身後諸将。
“衆人參軍入行伍,受國家俸祿,當為國報效,英勇殺敵,保國安寧!”
“吾輩将士,能否做到臨陣不懼,視死如歸?”
他震聲向部将吶喊,訓話。
在他面前的,是長長的騎兵部隊,衆人紛紛拔出腰間長刀,金鐵交鳴聲齊齊響起。
“能!”
大軍齊聲吶喊,聲震四方。
“為保家國安寧,為保百姓安康,諸位能否确保,将敵寇賊虜殺光趕盡?”
“能!”
“我蜀地男兒遠征北方,諸位能否做到,為我蜀地百姓争光奪彩,奮勇殺敵,得舉國百姓稱道贊揚?”
“能!”
一連問了數個問題,調動起全軍将士心中熱血,李恪再次打馬轉身,迎向城門。
此刻旭日初升,秋風卷起地上塵砂,迎面打來。
李恪閉眼感受着太陽初升的溫度,重重地吸了一口氣。
“全軍出發!”
他振聲而喊,随後,全城百姓随他一起吶喊歡呼:“全軍出發!”
“全軍出發!”
整個成都城都在吶喊,聲聲吶喊中,一支部隊出城北上,迎着初升的旭日,奔赴戰場……
084 商讨和談?
突厥特使阿史那·巴坎近來的日子過的很舒坦。
自從到了長安之後,他每日聲色犬馬,恣意享樂。
那鴻胪寺卿正仿佛當他是祖宗一般,每日好酒好菜伺候着,不時還要來親自問候,生恐他有什麽不滿意。
便是禮部尚書窦盧寬這等朝堂大佬,在他面前也是溫言細語,态度恭謙。
回想那日在朝堂之上,大唐諸官對他是橫眉冷目,态度強硬,當時他還道這趟出使怕是不能得償所願。
可這幾天,看接待官員對他這般悉心伺候,阿史那·巴坎心中已有了數。
這大唐的底氣不足,定是不敢應戰。
這自然是合了阿史那·巴坎的心意,他出使大唐,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,動用他那靈巧的嘴皮子,将大唐的大片領土給逼過來。
打仗不還是為了錢糧土地嘛!能少費點力氣,何樂而不為呢?
于他個人而言,打仗贏來的收獲,那是三軍将士的功勞,但一旦雙方達成和談,那可就是他阿史那·巴坎出使有功了。
雖說時間一天一天過去,可阿史那·巴坎對達成和談還是很有信心。
總得讓李世民那老小子矜持幾天吧?
否則他面子上怎麽挂得住?他怎麽向大唐的子民百姓交待?
阿史那·巴坎心中斷定,對方一定會在五日之內,前來商議和談細節。
若非如此,那窦盧寬何必要如此盡心盡力地伺候着呢?
再說他自己心中也清楚,這幾日他在長安,那是吃拿卡要,樣樣可都沒手軟,而且不光吃人家的,喝人家的,态度還十分高傲,一般人早就受不了了。
可大唐的官員還這般恭敬侍奉,這不已說明問題了嗎?
今日是和談期限的最後一日,阿史那·巴坎已在期待,這窦盧寬也該過來,傳達大唐的和談請願了吧!
悠悠往堂中胡床上那麽一靠,阿史那·巴坎又抿了一口茶水,哼着小曲兒,等着窦盧寬的到來。
這茶水又酸又瑟,實在是不那麽好喝,他肚子裏的饞蟲又活泛起來,拿眼睛搜尋着堂中是否還有好酒。
前幾日,這大堂之內,每日都是好酒好肉擺着,美人兒在旁舞着,那可真是美得喲!
一想起這幾天的好日子,阿史那·巴坎不禁又嘬了嘬嘴唇。
可他最終還是忍住了,又吞了口茶水,打消了再享樂的念頭。
畢竟今日是商定和談協議的日子,他可不能叫酒色給迷了心智。
“唉!還是等談完了正事兒,再喊那小美人兒來消遣消遣,嘿嘿!”
正兀自嘆着,堂外已傳來的急匆匆的腳步聲。
“咚咚咚”的敲門聲響起,随後傳來了窦盧寬的聲音。
“特使大人……特使大人?”
這是窦盧寬在屋外問候的聲音。
阿史那·巴坎清了清喉嚨,而後拖長嗓音,用慵懶又無所謂的語調哼道:“誰啊?進來吧……”
這雙方談判,得擺個譜兒。你要作出一番無所謂的态度,人家才會巴巴地哄着你……
若你顯得太積極,說不得人家在談判時,底氣就足了。
阿史那·巴坎自認為自己尺度拿捏得恰到好處,不禁得意地笑了笑。
“吱吖~”
門應生而開,窦盧寬大步走了進來。
這窦盧寬今日穿了一身紫紅官袍,顯得格外正式莊重。
這是自然了,來商讨和談事宜嘛,自然得莊重些咯……阿史那·巴坎心中一笑。
将腳往胡床上一搭,随手捏起茶盞抿了口茶,阿史那·巴坎才悠悠開口道:“窦大人,今日來此,有何貴幹啊?”
窦盧寬輕咳兩聲,說道:“本官今日前來,乃是與貴使談一談,你北方三國犯唐之事。”
阿史那·巴坎心中一樂,這老小子,終于沉不住氣了……
咱得擺點譜兒,可不能叫你大唐輕松過了咱這一關!
心中這般想着,阿史那·巴坎将頭一側,伸手撓了撓耳朵,擺出一副悠悠然的模樣。
“既然窦大人要談,那便談吧~”
拖長聲音回應着,阿史那·巴坎仍未起身,保持斜趟的姿态。
他這副姿态,當真沒有一點想要商談的意思。
“咳咳,特使大人……”
窦盧寬略一皺眉,看着阿史那·巴坎道:“既然是商談正事,還是請坐直身子吧!”
阿史那·巴坎譜也擺夠了,他心想這和談之事才是重點,便也一抖雙腿,将腳放了下來,而後坐直了身子。
“談吧……”
他伸手一指,指向堂內的客座。
窦盧寬一撩官袍,端端正正地坐了下來,他正色道:“特使大人,你三國聚集衆兵,犯我邊關,侵擾我大唐百姓,這等行徑,乃是人神共憤,天理難容的!”
一開篇,窦盧寬便開始譴責北方三國,将他們的侵略行徑大加貶駁。
這些話說得铿锵有力,但聽在阿史那·巴坎心裏,卻都化成了為和談争取主動權的話術。
這大唐打又打不過,就知道整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,其目的嘛,自然是為了争取道德至高點,想辦法少賠些錢財土地咯!
窦盧寬常年研習漢人風俗,早就将這種談判話術研究得透徹清晰。
他絲毫不慌,先讓窦盧寬一頓輸出,反正他突厥人向來是不在乎什麽出師有名,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,哪有錢糧土地重要呢?
便讓你大唐在道義上占些便宜吧!
阿史那·巴坎默然不語,待窦盧寬說得累了,他才撓了撓耳朵,将那一通廢話清理出去。
“好了,窦大人,說了這麽多,您也累了。”
“還是直接點吧!你們大唐準備賠多少錢糧?”
還不待窦盧寬說話,他又補充一句:“醜話我可說在前頭,這黃河以北的土地,盡歸我北方三國。這一點可是三國早已商定的,不容你讨價還價!”
說完這些,阿史那·巴坎往胡床上一靠,等着窦盧寬來商讨錢糧之事。
他心中已有了打算,土地才是最重要的,至于錢糧,三國聯盟并未有硬性要求。
但倘若能多拿多占,他當然是要争取的。
這具體的數目嘛,就看雙方讨價還價了。
085 衆軍集結,開戰
阿史那·巴坎還等着窦盧寬讨價還價,他心道大唐肯定是不願意多賠的,可大老遠跑一趟,不掙點銀子回去,實在有些不大爽利。
卻見窦盧寬這時候看了過來,他目光凜凜,神色淡定,倒有點六部首官的風範。
“特使大人,這賠償嘛……我大唐一分都不會出!”
窦盧寬正色而道,話語铿锵有力。
“什麽?”
一聽這話,阿史那·巴坎登時便坐直了身子,尖着嗓子叫道。
雖然他對錢糧之事并不上心,但也沒想到大唐竟一文錢都不肯出。
“窦大人,你可要想清楚了,惹怒了我北方三國,那下場可不會太好看!”
他恨聲威脅着,心中已有了怒意。
“不錯!本官說得很清楚!這正是我大唐天子的态度!”
窦盧寬神情堅毅。
“好!好!”
阿史那·巴坎心中已是不悅,但他還不好發作,畢竟土地之事才是要點,達成和談才是最重要的。
心中思慮一番,他将牙一咬,擺手道:“罷了!錢糧之事,咱們再談。這土地你們是答應割讓了吧!”
他已算計好,先将土地之事敲定,這錢糧的問題,回頭還要再磨他一磨。
土地之事,阿史那·巴坎覺得十拿九穩,畢竟大軍壓境,給了大唐極大的威脅。李世民心中也該清楚,要想三國退兵,割讓土地是逃不掉的結局。
可窦盧寬這時讓是不改威色,昂首哼聲道:“特使大人,我大唐的土地,一寸都不會給!”
土地也不給?
阿史那·巴坎氣得腦門生煙,他恨得渾身燥熱,來回看了一圈,最終抓起那茶盞,重重地往地上一掼,摔出清脆的碎裂聲。
“哼!這也不給,那也不讓……你們大唐拿什麽和談?難道就腆着你那張老臉去求我大軍退回去嗎?”
錢糧不給也就罷了,土地還不想給,阿史那·巴坎實在也想不出,大唐還能給得起什麽東西,能滿足三國,讓聯軍退兵。
“特使大人,我想你是搞錯了吧!”
這時,窦盧寬一撩衣袍,站了起來,他橫眉側目,淡淡道:“我大唐什麽時候說過,想要和談的?”
他這話如晴天霹靂,在阿史那·巴坎心中重重地劈了一道口子,阿史那·巴坎眼看對方一直恭敬,還道和談之事已八九不離十了,卻不想人家特意跑過來,是告訴他不打算和談的消息。
“你……你……氣煞我也!”
阿史那·巴坎也跳了起來,指着窦盧寬罵道:“你個老貨,當真是帶種啊!你可知道,我三國聯軍一旦出動,傾刻間就能打到這長安來……”
他又重重地哼了一聲,将頭一昂:“到時候……只怕你大唐李……天子過來,求着咱們割讓土地,咱們還要颠量颠量……”
他氣憤之下,下意識想直呼李世民的大名,可話到嘴邊還是縮了回去,他畢竟身在大唐,真惹惱了對方,只怕要被砍了祭旗了。
罵了一通,他仍不死心,又問道:“你大唐……當真不和?”
窦盧寬将寬大的袖袍一甩,昂首道:“當真不和!”
說罷,他又轉過身來,正對阿史那·巴坎:“本官勸你回去通知北方三國,若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