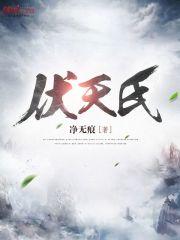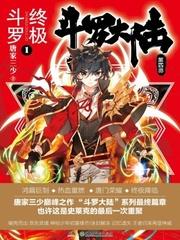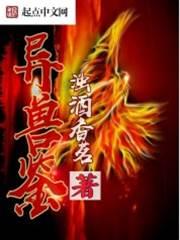16 又得浮生一日涼
趙興還在看着石灰牆感慨。
世界第一石灰牆呀,我竟然有機會站在牆下——扣牆皮!
感謝蘇東坡。是他,讓我們在這個喧嚣忙亂的時代,依然能感受到一絲曠朗的清風迎面吹來;是他,讓我們再回首,重新走過一段美的歷程。
這時代,文人士大夫都喜歡醉情于山水——比如蘇東坡的老師歐陽修最喜歡說的那句話“醉人之意不在酒,而在乎山水之間”,而唯有蘇東坡能靜下心來,觀察百姓的市井生活。
據說,他在谪居黃州期間,有一個老婦人因為賣不出去豬求他幫忙,他替老婆婆寫下了那首有關豬肉的廣告詩:“黃州好豬肉,價錢等糞土。
富者不肯吃,
貧者不解煮。
慢著火,少著水,
火候足時它自美。
每日起來打一碗,
飽得自家君莫管。”
蘇東坡這首詩裏隐藏着一種豬肉的做法,依法烹調出的豬肉就是中國名菜“東坡肉”。
唯有這樣一個關注市井的人,才能發現市井百姓所使用的“粉筆”,然後才能想到用石灰刷牆。如果古代中國的文化精英都像他一樣觀察市井,那麽……
趙興心有所思,回答蘇轼的問題顯得有點心不在焉,再加上他确實說不出自己的師承來歷,所以回答變得不着邊際:“門生出身于鄉野,所會所能,無師自通也!”
蘇東坡流露出訝然的神情。
或許,這種訝然帶有點輕蔑,或許,是趙興的學生誤會了,他們看到蘇東坡不信任的神色,程爽忍不住跨前一步,驕傲的說:“吾師學的是武侯遺學,惜當世無人能識,故自謙學究天成!”
Advertisement
“武侯”——這名字正捎到蘇東坡癢處,他是四川眉縣人,武侯正是川人最敬仰的人物。蘇轼立刻悚然動容:“你去過蜀地?”
趙興拱手答:“青城天下幽,峨眉天下秀!”
四川可是蘇東坡夢魂纏繞的地方,他自從出了四川後,終身未能再返故鄉。
為何如此?
為了避嫌!
蘇東坡的遭遇傳到四川後,有個四川人認為朝廷待他不公,或者說:以朝廷待川人蘇轼不公的名義發動了“起義”,他并不是希望起義成功後迎接蘇轼回鄉,而是希望成功後自己坐上龍庭。随後,朝廷費盡周折才把這場叛亂鎮壓下去……
此後,蘇東坡終生不敢提回鄉,結果他死在常州,葬在颍川。
蘇東坡是輕信的!
宋代是一個宗法社會,什麽叫宗法社會。在古代交通不便利的情況下,古人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未經批準前往外地的。當時也沒有電影錄像,如果一個古人知道外地的情況——哪怕是知道片言只語,也只能說明,他絕對在當地待過。
趙興僅僅一句簡單的詩文,蘇轼就确信面前這人确實在四川待過,他一聲嘆息,長吟思鄉詩——
“蝸角虛名、蠅頭微利,算來著甚幹忙。
事皆前定,誰弱又誰強。
且趁閑身未老,盡放我、些子疏狂。
百年裏,渾教是醉,三萬六千場。
思量、能幾許?憂愁風雨,一半相妨。
又何須抵死,說短論長。
幸對清風皓月,苔茵展、雲幕高張。
江南好,千鐘美酒,一曲《滿庭芳》。”
聽到趙興介紹表字“離人”後,蘇東坡更高興了,他翻箱倒櫃,摸出一件手稿,神神秘秘的問:“此詩稿被我去年中秋寫成,離人讀過這首詩嗎?”
詩寫的什麽——“春庭月午,搖蕩香醪光欲舞。步轉回廊,半落梅花婉娩香。
輕雲薄霧,總是少年行樂處。不似秋光,只與離人照斷腸。”
趙興不自覺的念出他最欣賞的幾句:“輕雲薄霧,總是少年行樂處……妙!絕妙!”
其實蘇東坡問的不是這個,他這首詩裏最後兩個字是“離人”,谪居黃州之後,他在感慨自己是背井離鄉之人,偶然遇到趙興,看到對方狂熱崇拜的架勢,他以為趙興是因為讀了這首詩,心有同感,所以取字“離人”。
拿出這首詩時,蘇東坡是很得意的,趙興的表現的像自己的鐵杆粉絲。這讓他飽受世态炎涼煎熬的心感到溫暖,所以他才不顧危險,拿出詩稿。
為什麽說“他不顧危險”?
通過交談,趙興知道了蘇東坡為什麽會出現在浠水,是因為貧與病。這位在浠水邊逢人便問鬼故事的孤獨老頭,剛遭遇了一次出賣與背叛,大科學家沈括利用他的信任,騙取了他的詩作,而後獻給朝廷,斷章取義地說他寫詩諷刺朝政,也幸虧高太後是他的絕對“粉絲”,竭力替他開脫,才使他僥幸躲過了死刑。
貶谪到黃州後,蘇轼生活窮困,曾前往蕲水(浠水縣)求田,希望自耕自種讓家人不再挨餓,不遂。後在故人的照顧下,在黃州得到東城門外的荒坡(東坡),開墾荒地,“東坡居士”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。
年老書生拿筆的手用來揮鋤,文弱的身體要養活一家幾口人,因為耕作勞苦,蘇轼患上臂疾——現代說法是“肌肉拉傷”,不得不前往浠水神醫龐安時家治療,因而常在浠水徘徊。
那一年,蘇轼48歲!
烏臺詩案後,蘇東坡貶谪在黃州,得了一個閑官:黃州團練副使(相當于民兵副隊長),正處于監視居住的待遇,地方官按期來到他的住處,檢查他的言行以及書稿。為了避禍,蘇轼将很多詩稿悄悄焚毀,一小部分被兩位倭人偷偷藏起,到蘇轼複出這些詩稿才重見天日。
所以蘇轼現在把詩稿拿給陌生人看,實在是件極具勇氣的事——也是對趙興極大地信任與肯定。
趙興感懷蘇轼的坦誠,他只顧贊賞詩句之美,卻把詩句中的“離人”兩個詞忽略過去,蘇東坡孩子脾性犯了,他用指頭使勁敲打詩稿上的“離人”二字,就等對方評價。
這首詞的最後一句也很不錯,趙興嘆了口氣:“你我皆‘離人’!”
只這一句話,便拉近了他與蘇東坡的關系。
又聊幾句,趙興想起剛才的疑惑,反問:“為什麽是‘也’……我是說,你剛才問‘我也參加取解試’嗎,為什麽是‘也’?”
※※※
蘇東坡沉默片刻,黯然的回答:“吾子邁也将參加今年的取解試。”
蘇邁确實參加了這一年的取解試,通過取解試後,他沒有繼續參加省試,而是到了臨近縣當了一名縣尉,從此以吏員的身份在大宋官場輾轉。
說起來蘇邁去當縣尉,還與一篇偉大的作品有關,蘇東坡親自送蘇邁去赴任,并繞路前往石鐘山,與兒子一起探究石鐘山叩石作響的原因,後來寫下了著名的《石鐘山記》。
蘇東坡的這番考察是在體驗用實踐的方式考察理論。這實際上是一種科學實驗手法,而且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篇科學考察報告。然而,士大夫們沒有注意到他所使用的科學推理,所以中國沒有系統化的科學體系。
一起參加取解試,不知道能不能算做“同年”,趙興生恐自己說錯了話,他只是默默的向蘇邁拱了拱手,見到那個老實人也沒有說話,他轉過頭來詢問蘇東坡:“邁兄應試,我等當避你鋒芒也。”
蘇東坡哈哈大笑起來。
這句話其實說得是蘇轼。當年蘇轼進京趕考的時候,歐陽修看到他的詩文,立刻大驚失色,說“此子将來必定不凡,我當為他避路而行”。如今趙興用這句話來說他的兒子,令蘇東坡很開懷。
其實,蘇邁這時的離去也是一種無奈。蘇東坡因為生活困窘,他就按照農村人的通常做法,讓成年的大孩子出去自立門戶。而蘇邁這一走,因為生活所迫,他再也沒有回到父親身邊,《石鐘山記》是他對父親最後的記憶。
正因為這個原因,蘇東坡笑得有點苦澀。
這是一個悲情人物,趙興雖然不了解情況,但他從蘇東坡苦澀的笑臉約略猜出對方的困境,他有一點黯然,不知道該說什麽好。
倒是蘇東坡開朗,他一會便把話題轉過來,與趙興聊山水,聊詩歌……還聊鬼。
“什麽?你不通詩賦?”蘇東坡感到難以置信。
這時代沒有拼音,沒有字典,人們識字全靠老師口口相傳,識得字越多,代表對方看的書多。趙興剛才讀蘇東坡的詩,讀起來毫無磕巴,蘇東坡不信這樣的人居然不懂詩歌。
還是王夫人進來解了圍,她笑着扯扯丈夫的衣袖:“官人,離人學的是經天緯地之學,豈會把精力放在尋章摘句上。”
王夫人就是王夫人,現在房間裏放不下屏風,但這位王夫人也學了她姐姐的作風,一并躲在一邊傾聽這番對話,以便幫助丈夫判斷客人。
蘇東坡一貫聽夫人的,尤其在識人方面,他稍稍一呆,立刻想到對方看見滿屋雪花時那離奇而跳躍的思維,便附和的點點頭。
明白雖明白了,但他好為人師的癖性不改,立刻從床下翻出幾本詩詞格律要給趙興講解。然後……
趙興一聽到詩詞,立刻覺得頭皮發炸,直打瞌睡。但他态度是恭敬的,眼神是漂浮的,心思是不在詩上的……
蘇轼肯給他講詩詞,這說明什麽。這是莫大的機遇。
雖然蘇東坡是官場倒黴蛋,但他教出來的“蘇門四學士”個個名聲赫赫,接受蘇東坡的教導,哪怕算不上蘇門五學士,算做蘇門一條犬,也是莫大的榮耀。
王夫人這時進屋,是請他們吃午飯的。托趙興的饋贈,這頓午餐豐富的足以待客了。見到蘇東坡半天沒有滅去做老師的心思,王夫人忍無可忍,打斷了蘇轼的興致:“官人,今日有酒有菜,離人難得來,有話何不日後再言……”
……
接下來幾天,趙興忙于取解試,無暇登門求師,恰好躲過了蘇轼的訓導。
黃州當時是個極為閉塞的地方,蘇東坡在給友人的信中,戰戰兢兢的寫到:“黃州真在井底,杳不聞鄉國消息!”趙興沒有想到,在黃州這樣的偏僻地方,應屆考生居然能達到500餘人。由此推而廣之,宋代應試的舉子是個多麽可怕的數字。
現在考古認為:宋代平常年間,每年應試的舉子是四十萬。
四十萬,現在人想象不到這個數字有多麽恐怖,這說明達到高中水平的應屆畢業生有四十萬,而與此同時,那些有文化而沒有參加考試的人,其數字……哪怕是粗粗測算一下,也是駭人聽聞的——它相當于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總人口數。
宋代是一個中古世紀信息量爆炸的時代,拜印刷術發達的技術進步,當時,國民教育已經進入了普及教育階段……
黃州偏僻,取貢士的比例是八十比一。這也意味着,程家坳三人中舉,幾乎占去了本屆貢試的二分之一名額,考試結果一出,整個黃州轟動。
可這些身外榮耀,趙興已經不在乎了,貢試過後,他着急的領學生拜訪蘇東坡。每日态度恭敬,但絕不接受教導。
在他的熱情之下,蘇東坡終于允許他執弟子禮,呼自己為“師”。不過,令蘇東坡憤恨的是,面前這個愚頑不靈的漢子,雖然學習态度很端正,但學習詩詞格律的進度幾乎為零——在這一方面,他甚至不如自己的學生程爽程夏。
要知道,蘇東坡貶谪黃州期間,尤其是他貶谪黃州第三年以後,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時期。過去他雖然有起落,但詩名還在,依然有無數的追随者,而黃州詩案之後,他因詩獲罪,政府剝奪了他寫詩的權利,由此,他便成了一個披着蓑衣、拄着竹杖,滿大街詢問鬼故事的困苦老頭。
初來黃州時,還有人肯送學生來聽他教導,四年過去了,他的學生盡受牽連,沒人敢再求教于他。
ps:因為要快速鋪開背景,展開情節,所以有些地方沒有展開來說,請理解。至于蘇轼,不能以現代男人一夫一妻标準去要求他,所以,在當時他對女人的方式并不過分。宋代的女人有很多打工方式,請慢慢看了就知道了。
※※※
在這種情況下,趙興帶着兩名學生闖入他的視野。這個人沉默寡言,但蘇轼能感覺到對方那份真誠,而且趙興總是用仰慕的态度謙恭對他,使蘇東坡重溫了那份詩豪自傲。
就在此時,也僅在此時,他才允許這樣一個對詩詞歌律一竅不通的人,對他執弟子禮。過了這段時間,數以萬計的人打爛頭求他教導,他還不屑一顧。也因此,他愈發對趙興的學習态度不滿。
從趙興的表現看,這個人也并不是不欽佩他的詩才。然而,憑心而論,趙興實在不是學詩的材料。他本來就對宋代發音非常頭疼,再讓他去講究字的韻腳,簡直是酷刑。
努力了幾天,蘇轼放棄繼續教導這個詩歌蠢材的努力,他又恢複了自己的日常作息習慣:每天早晨披上蓑衣、戴上鬥笠、荷一根竹杖,縱情于山水之間,而趙興也每天像上班一樣,有規律的來蘇轼這裏報個到,幫兩位夫人做做家務,而後留下兩名學生在“雪堂”讀書,自己一轉身跑個沒影。
時間長了,蘇轼也摸清了規律,未免看到趙興生氣,他每天早晨出門,臨到下午,走累了便返回家,順便教導一下趙興那兩名學生。
今天他回來的比較早,正午就回家了。進門時看到趙興,只見他剛剛走出黃州城門,神态很悠閑地背着手,身後牽着一頭小牛。
這段時間,趙興消失了四五天,而程家坳的學生不停往蘇轼這裏運送一些建房的材料。蘇東坡隐隐猜到了對方的意圖,但他性子比較粗疏,此事僅僅往心裏一過,便被丢在腦後。
王夫人對院內不斷增加的建築材料倒是問起過。兩名孩子對此的回答是:“冬天快到了,師姨娘就要生了,老師擔心江邊風寒露重,所以打算建一座磚屋,讓師公過冬……老師嗎,去了泉州,說是打算‘觀光’……”
師姨娘、師公、觀光,這幾個詞在當時還沒有出現,兩個孩子的說法讓王夫人楞了一下,但她眼珠一轉,便明白了此話的含義。
王夫人繼續打聽,甚至還搞到了幾張趙興手繪的建築圖紙,不過這圖紙她看不懂。對她來說,趙興繪制的房屋,造型很怪異。而趙興,據說這段時間正在泉州雇工匠,并與工匠探讨蓋房問題。
蘇東坡對趙興的多事采取不以為然的态度,王夫人私下裏提過幾次,無非是“受恩太重,無以回報,恐其心理難測”等等,但看到幾個孩子一副理所當然的态度,而蘇東坡幹脆裝糊塗到底,她便不再唠叨。
蘇轼的早歸是因為“收獲”。現在撞上趙興,他顯得很有點興致勃勃,扯住後者衣袖說:“離人,我今天出去又作了一首詩,你聽聽——
林斷山明竹隐牆,
亂蟬衰草小池塘。
翻空白鳥時時見,
照水紅蕖細細香。
村舍外,古城旁,
杖藜徐步轉斜陽。
殷勤昨夜三更雨,
又得浮生一日涼。”
背完這首詩後,蘇東坡沾沾自喜的問:“此詩如何?”
他如願以償了——趙興眼裏閃着狂熱的目光,他激動的發抖,仿佛情感無處發洩,他轉身抓住兩只牛角,拼命的晃晃,然後說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話:“又得浮生一日涼——我在這裏,我在現場!我看到了……我愛死它了。”
這種狂熱的追捧,蘇東坡以前經常見。曾經有一次,他随朋友在江上夜游,有名三十多歲的婦女專門駕船趕到他的船邊,彈一首琵琶請他做詩,于是便有了《江上琵琶女》這首詩。
連當今皇太後都是他的狂熱粉絲,這種天皇巨星待遇他以前經常品嘗,趙興的激動讓他回溫了過去的輝煌,他很自得的轉過身去,像君王回宮般向他的破屋。
他确實是一位君王,文學界的君王,詩壇的君王。
趙興還在興奮地扯住牛角,拼命的搖晃,小牛被扯的呶呶直叫,一名過來圍觀的小孩看他的奇怪舉動,很純真的問:“興哥兒,你在幹什麽?”
這個小牛不足三個月大小,牛角還很稚嫩,看到趙興的舉動,誰都會誤會他,是想空手把小牛的牛角拔下來。
趙興蹲下身來,溫和的向這名孩子說:“我在激動!”
倒也——那孩子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這是蘇轼的二兒子蘇迨,王閏之生的長子,當年14歲。
蘇迨在蘇轼所有的兒子中最為怪異,據蘇氏族譜記載,他以蘇炳的名字參加了取解試,而後以蘇昺之名任饒州太常博士——這個名字他也只用了一年,1094年他又以蘇鼎之名,考中哲宗紹聖元年甲戊連科捷進士。
此人一生用了四個名字,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。現在推測起來,也許他是因為蘇轼遭受文字獄,希望改換名字,以免受株連……
當然,這僅僅是一種猜測——後人無法想象文字獄時代的生存難題。
蘇迨揚起小臉,望着這位身材高大的師兄,指指這頭小牛說:“離人哥哥,你幹嘛牽這頭小牛來,剛才朝雲姨姨說:我家可養不起這樣的小牛,還需兩三年它才能下地幹活……要費很多糧食哦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