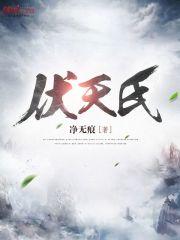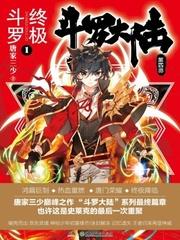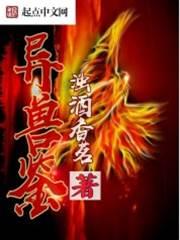25 空前絕後的一句話詩人
樸寅光不願意了:“賢侄,怎可如此戲耍老夫?在場的有百餘人,親耳聆聽,難道他們都聽錯了?”
趙興郁悶的躺回床上,他蒙着頭,躲在被窩裏使勁想——這誰幹的?
被窩外,樸寅光循循善誘的唠叨着,說的什麽,心煩意亂的趙興沒有聽清。
其實,趙興也曾是在中國式教育下長大的,他也接觸過許多唐詩宋詞。但接觸過蘇轼這樣的巨人之後,讓他的膽子變小了許多,他不敢在宋人面前賣弄文采,所以決定終身不做一詩。
這一方面,是時間久了,他無法确定自己記憶中的那些詩歌作者是誰,所以擔心讓人看出剽竊行徑。另一方面,是考慮到詩歌這個東西,于國于民毫無用處,所以幹脆藏托。然而這首詩的出現卻打破了他的戒律。
這首詩是誰做的,他現在壓根想不起來,拼命搜索記憶,只記起它似乎是一本暢銷書中提到過的詩句。他竟然将這記憶深處的詩詞背誦的整句不差,現在想起來,他都對自己的記憶感到驚詫——如果讓他現在再背一遍,也不會記的像昨晚酒醉後那麽鮮明。
樸寅光唠叨了許久,趙興将頭拱出被窩,用一個詞解釋了他的回避與躲閃——“烏臺詩案”。
樸寅光恍然。
蘇東坡因詩獲罪,臨出京時,他的妻子将大部分詩稿焚之一炬。因為這場文字獄的牽連,很多沾邊的人都受到了流放,在這種情況下,身為蘇轼門生的趙興不願意用詩才名動公卿,也是不願替蘇轼惹禍的小心。
“壞事,壞事……我馬上通知在場的官員,讓他們守口如瓶”,樸寅光趕緊向外面跑,沒跑兩步,他停止了腳步,又看看手中書稿,搖搖頭補充說:“沒有犯忌的呀?!”
他忘了,趙興是身在高麗。到國外去寫詩,沒有犯忌,別人可以給你扣上犯忌的罪名。
這首詩是清代詩人納蘭容若寫的,是一首悼亡詩,紀念他亡妻的。
趙興是在歡迎他的宴席上吟誦這首詩的,詩的第一句“人生若只如初見”一下子就抓住人心,這首詩的性質全變了……
樸寅光的出面勸解使高麗國內對蘇轼充滿了同情,他的門生都如此小心謹慎,可以想象蘇轼在國內是個什麽處境。
趙興沒有發現,他原本是想防止別人發覺剽竊行為的保護措施,卻間接為他造成了更大的影響。在整個高麗文壇,人們都悄悄的傳頌着那首詩,知情者把他奉若上賓,在與他交易的過程中,完全不在意價格,以近乎免費的方式任他選購。
比如現在,趙興坐在宴席上正蒙着頭吃烤鳥,左右卻在竊竊私語:“哎,那個低着頭吃烤鳥的傻鳥是誰?”
Advertisement
“什麽,你竟然不知道他?孤陋寡聞了吧,你!讓我來告訴你……人生若只如初見……怎麽樣?”
然後是恍然大悟的“哦哦!”,片刻過後,又是疑問:“不對呀,這麽好的詩,怎麽是一只傻鳥作出的?他像嗎?”
什麽像不像?趙興郁悶的發狂,這種竊竊私語每次都有,還讓不讓人吃傻鳥了?
原本趙興是不打算在參加這種應酬,但實在是……他的色心讓他舍不得放棄這樣的宴會。直說了吧:高麗人現在穿的都是唐裝,什麽是唐裝,就是黃金甲裏面的“爆乳裝”。真正的高麗服是完全仿唐的,極端擠壓胸部,暴露出雪白豐碩的“豐乳肥臀”。
現代人要看到這種情形,需要從高麗早期的壁畫上觀摩。因為在日本殖民時期,日本人認為這種唐式裝束有傷風化,故而取消了。
但現在,她們活色生香的浮動在趙興面前,就仿佛是畫中人物來到人世間一樣,誘惑的趙興不忍離去,不忍告別……
告別的日子終于還是到了,十日後,裝滿高麗銅條、金塊的貨船離港,岸邊,無數高麗士子峨冠博帶,站在江邊吟誦,場面宏大,他們齊聲高唱:“人生若只如初見,何事秋風悲畫扇?等閑變卻故人心,卻道故人心易變。”
這幾日一直躲在船上的趙興,帶着提心吊膽的笑容站在甲板上,與岸上的樸寅光揮手作別。
其實,高麗人不是單為送別趙興而來,他們送的是名詩人蘇轼的門生。而趙興也白擔心了,在這時代“人生若只如初見”的作者絕不會跳出來找他的麻煩。
船行出高麗外海,岸上的人還在高唱,只是聲音聽不到了。趙興呆了一呆,突然下令:“轉舵,目标遼國!”
篙師劉小二疾呼:“大官人,遼是敵國,萬一有人告發……”
劉小乙擔心的是船上的人告發。
“自高麗去遼國,最近,轉舵吧,都來到附近了,怎麽不去看看遼國,其他的,回頭再考慮!”趙興淡淡地回答。
※※※
臨近百啐,程族的人已在蘇轼院裏搭好了鍋竈與長棚,一切就緒,就等日子到來了。
四鄰的鄉民都巴望着這一天的到來,因為按習俗,過百啐的人家要給四鄰散福,并接受四鄰送給的百衲衣,以此祈求孩子的長命百歲。
按說,一個罪官不該如此張揚,禦史知道了會聞風彈劾,讓蘇轼的處境更加糟糕,但現在,強勢的程族出面操持,每人2貫的散福錢,徹底令府衙內的佐官雜吏閉嘴。
至于徐知州,那天酒宴後,他似乎欠缺節制,最近身體欠佳難以出席。但在他的默許下,在那一天,州衙的高級官員在收到一封大紅包後,那一天還将會被約到江對岸的武昌栖霞樓暢飲……所以,那一天他們将什麽也看不到……
最先發現趙興出現的是蘇迨。當時,趙興正一手拿着一本書,另一手牽着一頭牛,悠悠閑閑的出了城東門,蘇迨一見,立刻歡喜地鼓掌說:“好啊好啊,我家又要‘跌死’牛了。”
蘇迨的喊聲引來了蘇邁,他站在院門口等待迎接趙興,這才發現趙興雖出了城門,他背後一串長長的隊伍還在城裏。
※※※
緊随趙興身後的是一名騎驢的中年婦女,然後是一頂小轎,小轎背後是七八對挑籠箱的壯漢。
趙興進門時,王夫人也站在門口迎接,蘇東坡的三兒子蘇過很好奇的打量着趙興牽着的牛,問:“興哥,這次跌死牛,會讓我看嗎?上次,大哥二哥都看了,就我沒看到。”
趙興把牛繩遞給蘇邁,用溺愛的表情看着蘇過說:“這是乳牛,是用來喝奶的。”
蘇過繼續問:“它是那頭(‘跌死’)小牛的媽媽嗎?”
王夫人臉色變了一下,趕快扯過蘇過,捂住他的嘴說:“離人,這饋贈太厚,我們不該取。”
趙興不以為然,他鞠了躬回答:“夫人,我與學士之間何必計較……夫人如是過意不去,可把這兒當作賭約的一部分——願賭服輸,我這是償還賭債。”
王夫人不好再說什麽,再說,朝雲新生了孩子,他們經濟确實有點困窘。
王夫人讓開門柴門,仆人們流水般将禮物擡進院裏。這時,趙興身後的小轎落地,一名裝束齊整的小女孩下了轎子。王夫人趕快迎上去,牽住這女孩的手,笑着說:“這就是黃州人說的‘掌上明珠’嗎?我早聽說你長得俏美,可惜我近日為孩子所累,也沒去看看。”
蘇東坡聽到院子裏的聲音,他不好出去,只能端坐在自己書房,擺出老師的架子,等趙興帶着那名女子進來,向他行過拜師禮,他方矜持地點點頭。擡手示意王夫人帶着阿珠去廂房,自己放松了身子,責備說:“離人,帶那麽多東西回來,孩子百啐而已,這禮太厚了,為師……”
“恩師——‘有事弟子服其勞’,一家人,何必客氣。”
一家人,這話讓蘇東坡眼睛有點濕潤。況且,此時此刻,他也确實客氣不起來。
蘇轼是個灑脫的人,片刻後便坦然了,他立刻就禮節上的疏忽解釋:“離人,朝雲剛剛生産,身子弱,就不出來見客了。”
盡出親眷見客人——這是古人的禮節,表示與對方是一家人。
趙興理解,他回答:“我帶了一位乳母,還帶了一頭乳牛,老師的舊屋還在的話,就讓她們安置在那裏……冬天了,也好多個人照顧小兄弟。”
蘇東坡的三個兒子一直按禮節陪客,蘇迨孩子心境,聽到這話,趕緊跑出告訴母親,蘇邁一把沒抓住,只好歉意的一笑。
“一家人,無需太多禮節。”趙興寬和的笑着,朝蘇邁說:“我自倭國弄來幾把倭刀、幾副铠甲,伯達兄要去饒州德興做縣尉,正好用上——裝铠甲兵器的箱上,有用粉筆做得标記,大哥将那些箱子搬去自己屋裏吧。”
蘇邁話不多,拱手感謝。
蘇過已經忍了很久,初次見到趙興,他就吃上了肉,所以趙興給他的印象就是能帶來肉。現在,看到爹爹假意亂翻書,而哥哥只是拱手,并不說話,他忍不住眨着眼睛問:“興哥兒,我們今天不跌牛了嗎?”
趙興蹲下身來,笑着說:“我們今天不跌牛——跌驢,我把乳娘騎來的那頭驢給你‘跌死’,怎麽樣?”
“不可,離人不可嬌縱過兒”,蘇東坡馬上勸止:“這驢是代步,怎……”
趙興卻毫不在意:“老師,何必責備小兄弟吶。我也是聽說驢皮熬膠、加上紅棗,就是著名的阿膠,對産婦大補——這驢是我特地牽來宰的。”
他把我這裏當作屠宰場?
蘇東坡好生郁悶。
沒等蘇轼反應過來,趙興已把手裏的書扔下,拉着歡天喜地的蘇過跑出去。蘇轼追之不及,只好撿起趙興扔下的書,沖長子苦笑一下——這本書是《宋刑統》。
“跌死”驢,難道也要事先查看宋刑統?
此人做事如此小心,為什麽?
院內,驢已經捆起來了。捆驢的時候,蘇過很好奇的問:“興哥,我聽說上次牛跌死的時候沒有捆腳,這次你為什麽捆住驢的腳?”
答案是:趙興知道牛心髒的位置,不知道驢心髒的位置。他看的電視節目是介紹鬥牛的,鬥驢暫時沒有。
孩子問了又問,趙興哼哼了半天,答:“捆上腿的牛跌死了,衙役那裏需多花錢,而驢不用。”
說罷,趙興已把手裏的刺劍紮進驢的脖子,驢開始掙紮,由于血液湧進嗓子眼,它沒有扯起那著名的驢嗓子。這時,蘇過已忘了追求答案,只顧看驢掙紮。
蘇邁在趙興身邊幫手,趙興邊幹活兒,邊繼續向蘇邁交代:“我有個學生程濁,不喜讀書,但弓箭玩得很好,爬山走坡,快步如飛,伯達兄上任可着帶他,多少算個幫手。”
蘇邁點頭,謝過趙興的好意。
這次,趙興倒沒有接着表演他那首令人驚詫的解剖技巧,宰完驢後,剩下的工作都交給了孩子們,他則拉着蘇邁的手去檢點那些禮物。
趙興把現代的集裝箱理念帶到了宋代。這些禮品都裝在兩米長、四十公分寬、四十公分高的木板箱內,每只箱子上面都用粉筆寫這名字。
蘇轼得到的三個箱子,其中一個箱子裝的是瓷器,正是前面提到過的高麗翡瓷。另外的一只箱子裝的是高麗紙、日本紙、高麗硯等文化用品。
最後一只箱子比較特別,裏面裝了一把不帶刀镡(相當于我國通稱的劍格或護手),整體形狀像一截木杖似的日本杖刀。
箱子的空間很大,除了這把杖刀外,還有一件與其像蓑衣,不如說像藤甲的竹藤氅。剩下的空間則用高麗銅器填滿。銅器與銅器的縫隙間,除了鋸末稻草之外,趙興還塞滿了大量的銅錢、金塊、銀塊——對此,趙興的解釋統歸結為固定銅器。
以蘇轼的博學,竟然還不知道海上運輸還有這風俗,等他時候檢點,發現那些金塊足有五百兩,銀塊也有一百多兩,至于散碎銅錢更是多達數千枚後,他隐約猜到了趙興的想法,但他只是一聲嘆息。
※※※
給蘇邁的禮物是兩只箱子,趙興要回了那柄刺劍,回送給蘇邁四柄日本打刀、一柄太刀,還有十來柄解手刀,而後是三副備中産的铠甲,幾件皮甲……另一箱則是的高麗銅器。
送給兩位夫人的是成箱的綢緞。蘇迨與蘇過小,兩人分得一箱子的高麗玩偶。
蘇遁獲得的百啐禮最為豐厚,小孩需要的童衣整整一箱,然後是一箱布偶玩具、金銀鎖、金銀項圈……最珍貴的是一個玉盤外加一粒珍珠。
僅僅這一粒珍珠,立刻使蘇轼大驚失色,他慌忙拒絕:“離人,這東西孩子用不起,折壽了,你趕快收起來。”
兩位夫人微微露出詫異的神情,蘇轼卻沒有解釋,他嚴厲的用目光示意趙興。既然蘇轼不顧忌諱提到了折壽這個詞,又連連用眼色催促,趙興趕緊收起了這份禮物。
事後,蘇轼很嚴厲的叮囑在場的諸位,禁止将看到的東西說出去。看到蘇轼的恐慌,趙興明白了——他認識“走盤珠”。這位學者雖然從來沒見過“走盤珠”,但他看到那顆珍珠的形狀,立刻想起了相關傳聞。
既然走盤珠送不出去,趙興反手從身上掏出一個布囊,随手塞給王夫人:“這是學生在倭國買到的幾粒珍珠,比起剛才那粒差遠了,恩師且收起了,給夫人做幾副珠飾吧。”
蘇轼覺得很為難,趙興自始自終沒有表現出見外的神情,他是從心裏拿蘇轼當作了親人。只看他将價值連城的走盤珠都毫不顧惜的送出來,就知道這是位性情中人,他雖然表現出賺錢的急切,但從這個行為上看,他其實對錢財并不在意。
還要拒絕嗎?說實話,蘇轼想看看布囊裏的珍珠再做決定,但轉念一想,還有什麽珍珠比走盤珠更加珍貴,所以他猶豫了一下,用沉默的态度表示了默認。
他來不及反對,某位心急的客人已經來了,權衡之下,他把趙興的事放在一邊,急着接待客人。
程阿珠一直站在旁邊,從頭到尾一句話都不說,對于趙興的慷慨,她連眼睛都沒眨,她那雙似水的眼睛只看見趙興的存在。
趙興躬身告退,蘇邁從他的新收獲裏撿起一把解手刀,跟着趙興前去試刀,等到了驢身邊,他才發現孩子們手上都有一把類似的刀。他們也在做着蘇邁想做的事情——試刀。
刀很鋒利,有了蘇邁這位大人參加,不一會兒,屠宰工作已經完成,驢皮被切成小條,扔到大鍋裏熬煮,驢肉則被切成小塊,孩子們熟練的忙着腌肉熏肉,那些骨頭則被炖成了湯。
中午時分,客人三三兩兩的到了。代表徐知州出席的是一名小官,他帶來了徐知州的問候與禮物。
百啐宴是驢肉大餐。大塊的驢骨湯被分給四處鄉鄰,精細的驢肉則被做各種菜肴,端上宴席。
今日的主廚依然是趙興,這也是參加者最期待的事。上次在招待王鞏時,趙興曾經展露過一次廚藝,令王鞏在随後的中秋聚會上念念不忘,那些詩人朋友被他的描述所吸引,對趙興展示的美味垂涎欲滴。
奈何趙興的身份擺在那裏,不是誰都能逼他下廚的,更況且此人神龍一現,黃州城裏再也找不到他的身影……于是,所有受邀人都對這場宴請充滿期待,他們希望能證實王鞏的說法,并親身感受之。
這次他們如願以償,趙興展示出的手藝比上次還出色,因為經過這次海貿,他以最大限度的收集了各種香料(佐料),菜肴之豐富,花樣之繁多,令人嘆為觀止。
宴席進行到一半時,蘇東坡喚進趙興,很正式的向他的朋友介紹這位古怪門生:“諸位,這是劣徒趙興,字離人……離人,這位是黃州監酒樂大人樂京、這位是岐亭監酒胡大人胡定之,這是樊口詩人潘大臨潘君孚……”
趙興對前面的幾位官員不過點頭而已,但聽到潘大臨這個名字,驚問:“可是‘滿城風雨’潘大臨?”
一身布衣、卻坦然的坐在席上的年輕人不亢不卑的回答:“正是!”
趙興不為官員變色,而為潘大臨而動容的神情,正符合當時的風尚。
宋人都這樣,一個雖然沒有官職的白衣,只要他才華橫溢,寫了幾首絕代好詩,便可以大搖大擺的坐在官員滿座的酒席上,而官員們還要把他稱之為“白衣卿相”。
面前這位潘大臨不是因一首完整的詩而名動公卿的,那首詩他只寫了一句話:“滿城風雨近重陽。”
潘大臨字君孚,是個賣酒郎,早先在樊口開了個小酒店,打魚賣酒為生,蘇東坡谪居黃州期間,常過江到武昌找朋友玩,偶爾落腳潘大臨的酒店,喝過他釀的‘潘生酒’,寫下了“憶從樊口載春酒,步上西山尋野梅”,并寄書秦少游說“樊口有潘生,釀酒醇濃”。
潘大臨就是一個宋朝追星族,他性好讀書但屢試不第,故而終生未能出仕。聽到蘇東坡大名後,立刻搬來黃州——跟蘇轼學詩,并随蘇轼出游赤壁。《赤壁賦》誕生的時候,他也在場。後來,他沒有蘇門弟子的名號,但蘇門弟子之首黃庭堅稱他“蚤得詩律于東坡,蓋天下奇才也”,後來陸游也說他“詩妙絕世”。
這年重陽節前,潘大臨家中已經斷炊,只好饑腸辘辘地卧在床上。這時屋外秋風乍起,橫掃落葉。緊接着大雨滂沱,來勢兇猛,風雨交加,擊門敲窗。
見此情景,詩人忘記了饑餓,詩興大發,奮筆一揮,寫了詩的第一句:“滿城風雨近重陽。”
還要繼續往下寫時,有人敲門了——是債主上門讨債。詩人只好陪笑臉說好話,好不容易将債主打發走,可濃濃的詩意也随之而去。這次創作有始無終,留下了遺憾。
但也許是正因為這“遺憾”而使“滿城風雨近重陽”這句詩名揚天下,名傳後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