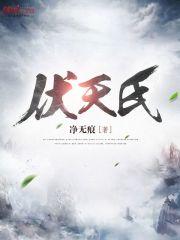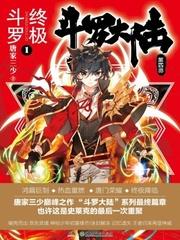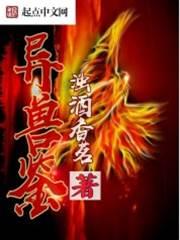31 難以拒絕的要求
任何時代,最缺少的是什麽?人才。
趙興現在确實缺人,為此他不惜大量吸納江夏程族的勢力。然而,萬事萬物都講究一個“制衡”,程族勢力過度膨脹,就必須引來競争機制。
陳季常要看趙興的武藝,顯然是早有打算,但也正中趙興下懷,他馬上應和:“太好了!我正籌劃赴杭州一行,黃州未免顧不上了,夢得叔來了,黃州交給你,季常叔的公子我帶去杭州……”
“恐怕我也照料不過來”,馬夢得笑着拒絕:“學士起複,我便打算随學士上任,所以你還是另找個人吧。”
“沒事,我還要在家待兩個月,這兩個月,夢得叔幫我教教孩子,等夢得叔走的時候,就把黃州酒業交給君孚(潘大臨)之弟潘大觀……君孚指望不上,這家夥心思不在操持家業上。”
潘大臨的失誤就在手頭無人可用,按說他一個酒店老板,手中擁有一個名酒牌子,最後卻混的那麽慘,實在不應該。如果他有人手可用,把酒店交給別人打理,完全可以自由享受宋代追星生涯,可惜他走了相反的路。
趙興沒有完全保密自己的“族方”概念,他擁有超越這個時代的“經理人”概念,本着專業事情讓專業人士負責的思路,他絕不放過對人才的搜羅,譬如陳慥的兒子,雖然不肖,但絕對是個合格的職業打手——他老爹的基因在那兒,這厮能差到哪裏?
至于馬夢得,也不能讓他閑着,經過趙興一番“勸解”,馬夢得終于全家搬進趙興的院子,“順便”幫趙興教育那群程族小孩,而陳慥因保甲風波,不敢過多停留,他匆匆告辭,回去安排兒子上路。
此後的日子裏,趙興忙着安排族裏的産業,蘇轼悄悄做好了起複的準備,馬夢得被一群孩子纏住,最麻煩的是僧佛印,他自此也多了個去處,不時上門來與馬夢得攀談,順便招攬一些贊助。
“佛曰:種如是因,收如是果,一切唯心造……”僧佛印打着稽首向趙興講解着佛法。
“且慢”,趙興頭痛的捂住自己的前額。天呢,這都幾次了,還讓不讓人活了。
“且慢,我知道你是來要錢的……對了,你們說這叫施舍,就是我舍棄財産施給你們,實話告訴你,我不信你們的佛,因為他是一尊收費的‘神’……這話你不懂?”趙興翻着白眼,痛苦難耐的說:“你也別勸我,我這人挺頑固。
這麽說吧,什麽時候,你們這些僧人為我誦經,不是為了我的錢包,而是真誠的希望我幸福,那我信了你們的佛又如何?”
趙興說話很無禮,如果擱別人這麽說,佛印必然開始施展恐吓、咒罵戰術,比如說:他會恐吓對方說神将懲罰他等等,或者直接開始謾罵。但面對趙興他們,他不敢如此,因為他偷偷看過蘇東坡寫的《刺牛》,那裏面描寫趙興幹淨利索的宰殺了一頭牛。
他知道趙興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,這樣的人才不會跟人對罵,或許他更願意用拳頭解決謾罵。
佛印正琢磨着如何措辭,趙興把話一跳,不問他佛禮,反而問起佛的行政級別:“我聽說,這世界總共有三萬多尊佛,天呢,我大宋有冗官之災,佛界會不會有冗佛之災?我聽說,有人曾經給這些佛爺劃分了行政級別,也就是說,如果我得罪了知縣級的佛爺沒事,只要我買通知府級的佛爺就行了。
Advertisement
當然,如果我不願意多出錢,那就買通另一位知縣級的佛爺,讓那兩個佛打架去,有沒有這回事?”
這話讓佛印很難回答,給佛劃分行政級別,這事确實有過,是五代時的“高僧”幹的,但出錢讓兩個佛掐架,這事只有趙興能想得出來——當然,百姓是這麽幹的,但他們從不敢這麽亵渎的思考。
趙興說起“五代”的事兒,突然間停頓了一下,他用回憶的口氣慢慢地說:“對了,大師是佛門高徒,你聽說過敦煌莫高窟嗎?”
提起這座佛學世上有名的藏經窟,佛印不禁精神一振,悠然神往的回答:“聽說過,聽說最近大食回教正在深入西域,這座西域名窟逐漸泯滅無聞,但我研究那座名傳天下的聖窟……”
趙興繼續用回憶的神情詢問:“我聽說,那座莫高窟裏畫着一幅壁畫,壁畫是一尊不知名的佛,手裏持着一個噴火武器?”
佛印不愧是佛界的優秀“公關經理”,他立刻補充說:“有這尊佛,施主真是廣聞——這尊佛名喚‘降魔’,此圖繪于五代,佛窟裏繪得形象是‘降魔十八變’中的一變,那件噴火武器名為‘降魔變’。是個銅管,這麽長,這麽粗……”
佛印用手比量着銅管的大小——這就是“降魔變”,世界第一支火槍。現代考古挖掘中,人們從黨項墓葬中挖掘出“降魔變”實體,它是一種形體粗壯的銅火铳,長35.3厘米、口徑10.5厘米、尾底徑7.7厘米,重6.94公斤,用火藥發射直徑0.9厘米的鐵彈丸。
1084年宋夏戰争中使用過——這是人類歷史上,火槍首次運用于戰争。
不過,“降魔變”并不是一種士兵“标配武器”,它是一種個例,是西夏軍官的特殊個人物品……然而,它的誕生代表着銅火槍制作技術已經成熟,差的只是捅破一層窗戶紙。
“銅管……?”趙興若有所思地說:“這樣吧,我知道你們佛門那些事,你們一定與西域僧人有聯系,別給我打馬虎眼,我既然跟你說這話,就一定有把握。
你不是來尋求捐獻的嗎?這樣吧,你幫我到西域找幾個會制‘降魔變’的匠人——佛門的東西,你們佛家一定跟這些匠人有聯系。我出個價吧,你招來三名匠師,我捐獻三百萬,如果這三名匠師技藝精湛,我再捐獻五百萬。
在黃州這個地方,八百萬足夠你起個樓、蓋個佛塔,怎麽樣?願不願試一試?你可以告訴那三名匠師,只要他們抵達黃州,我每人給他們一百畝地,一百貫安家費。造出‘降魔變’來,我再給他們每人一百貫。當然,造不出來,他們一個錢沒有,你們也沒有那筆獎勵。”
※※※
如趙興所說,黃州這地方窮鄉僻壤,佛門信徒的捐獻都是幾文錢幾文錢,如果佛印能拉到這筆施舍,完全可以徹底翻新鬥方寺。
佛印也潇灑,聽到趙興的要求,連“預付款”都沒有所要,他潇灑的伸出手,與趙興擊掌為誓,而後痛快的告辭,再然後,這個人便不再日日登門。
兩月後,趙興安排好黃州的一切,準備帶着程阿珠啓程前往杭州,臨走時蘇轼叮咛:“離人,我也感到朝廷這幾日起了變化,也許夢得兄說得對,我希望你快去快回,等我起複時你來幫我。”
“定當如此”,趙興慨然答應。
蘇東坡,大文豪,有這樣一個免費老師教導,想必他也能绉幾句歪詩。
臨到登船,趙興突然想起一事,回身交代:“老師,遁兒現在不足周歲,如此幼小,長途跋涉極不安全。如果我沒回來,先生就接到起複的消息,不如把孩子留下……這樣吧,阿珠留下,萬一學士走得急,便将孩子交阿珠照顧。”
蘇東坡仰臉朝天一聲長嘆:“離人是個能托妻寄子的人,把孩子托給你,我信得過。不過,阿珠還是跟你走吧,你倆新婚,多聚為上。”
“那好,我回頭交代一下程族長,再通知陳季常,有他們夫婦在,孩子一定會照顧的很好,老師可放心上路!”
趙興不知道,在真實的歷史中,蘇遁就死在跋涉的路上。他這一插手,歷史已經悄然改變。
元豐七年四月下,趙興的驢車進入泉州。與此同時,蘇轼送長子蘇邁赴饒州德興縣上任,寫下了《石鐘山記》。
這是個播種的季節,沿途,田野裏布滿了播種希望的農夫;這是個鮮花爛漫的季節,沿途無數說不出名目的鮮花讓初次走出大山的程阿珠為之癡迷。
泉州現在在外國人嘴裏稱作“刺桐”。泉州還有另一個名稱,叫做“光明之城”……一千多年前的夜晚,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漆黑,只有中國的城市燈火輝煌、光明燦爛;一千多年前的夜晚,全世界的城市都是一片安靜,只有中國的城市人流擁動、歡歌笑語……
世界各國,大多數城市都實行宵禁,夜裏禁止人們走上街道,然而,唯獨大宋準許商人徹夜營業,于是,大宋的夜晚是燈火通明、人潮湧湧的,從這個意義上說,大宋所有的城市都是“光明之城”。
這是個讓人熱血澎湃的年代,大宋的一切都在沸騰,翻滾着,沖擊周邊國家。21世紀,亞洲史學家充滿激動地記述:11世紀下半葉,亞洲是蘇東坡的亞洲,是大宋的亞洲。
此刻,正面對大家的是泉州北門。
趙興以前來過泉州,但他依然很癡迷的仰望着北門城牆。
這是一段很奇怪的城牆,城牆上,用城磚鑲嵌出天使與十字架的圖案,而北門城基呈現奇怪的尖拱形,上面鑲嵌出十字架和火焰、十字架和蓮花,此外還有15行阿拉伯(敘利亞)文字。
趙興作為現代人站在這裏,看着那些圖案總覺得很奇怪,他懷疑修建這座城牆的是一群基督教徒,因為不僅泉州北門鑲嵌有基督教圖案,泉州另外幾個城門、城牆,處處嵌有基督教的十字架,然而,在他的記憶中,不記的曾有相關的記錄,也許是蒙古人燒毀了一切文字,讓這段歷史顯得撲朔迷離。
現在,趙興站在這段泯滅的歷史面前,親眼目睹它的本來面目,他的心情卻難以用語言描述:驚詫?沉醉?欽佩?惋惜?遺憾?……更多的是濃濃的失落。
是的,他失落了什麽,這是民族的失落!
趙興不知道,蓮花十字架、火焰十字架正是中國本土基督教——景教的标志。這種十字架被人們稱為“刺桐十字架”,也就是“泉州十字架”。他所看到的那行阿拉伯文,是稱頌“聖父、聖子、聖靈”的。
身邊的人體會不到趙興的感覺,他們不停的催促他進城。趙興身後被他堵在城門口的人也連聲催促。在一片嚷嚷中,趙興垂下眼簾,舉步向城內走去。
一進泉州,首先看到的是無數用彩帛搭起的高大彩樓。在宋代,店鋪門前搭起的這種彩樓叫做“歡門”。沿着大街望過去,無數歡門争奇鬥妍,設計者的靈感令人嘆為觀止——在宋代,已經有了如此鮮明的廣告意識,實在令趙興難以想象。
趙興在泉州城門口處雇了兩個幫閑帶路。所謂“幫閑”,現在也可以稱之為“導游”,他們待在城門口,專門替外地人帶路,游覽泉州市內,并幫不熟悉地理的雇主處理一些瑣事。
這兩名幫閑是兄弟倆,老大叫劉小乙,老兒叫劉小二。他們殷勤地在驢車前,引領着整個車隊緩緩前行。熙熙攘攘的人群讓車隊行進緩慢,而程阿珠貪看風景,也有意識的命令車夫緩行,這讓兩名幫閑走的很悠閑,他們一邊領路,一邊跟車夫閑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