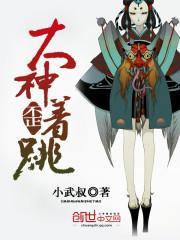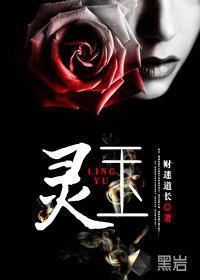26 (一更)
◎。◎
對于長壽的話題, 感興趣的可不只是嬴政。
朱元璋瞅着水鏡立刻冒出疑問,為什麽是始皇帝有超前的天文知識就能長壽?
咕咕是不是偏心眼?憑什麽自己就不行了!
不過,咕咕不知道水鏡投放到大明。
秦始皇能不能學到不好說, 自己能光明正大地偷師長壽秘訣了。
朱元璋懷着一絲竊喜, 繼續看了下去。
水鏡:
【聊天文知識對長壽的影響, 就要從古代對于天文學的定位說起。
古人重視天文嗎?
這個問題擱在幾十年前, 必定有國人不自信地認為古人不重視天文。因為古人不重視,導致當代發展落後。
彼時,中國對于太空探索尚不在國際前列, 而不可能幻想以購買代替自主研發,那必會遭到外國多方勢力的重重技術封鎖。
在百廢待興中,憑着我們自己的本領在航天領域闖出一片天來。
經過幾十年科學家們不停地努力奮鬥, 也依托于國力的日益強大,如今中國邁入了航天領域的國際第一梯隊中。
我想沒人會說航天沒用就是去天上看星星之類的杠精言論。
單說一條“掌握了航天技術, 也意味着具有發展彈道導彈全球打擊能力的基礎”, 你說它重不重要。①
Advertisement
話說回來,古人重視天文與否的問題, 從帝王将相層面來看, 是一直非常關注。
要意識到的是古代對天文的研究與現代不同, 其研究目的、研究範圍等都有差別。
帝王為何重視天文?是他們好奇蒼穹之上星辰的演化過程?
那可能占極小部分的理由, 但絕非根本原因。根源是古人認為政權天授。
漢代董仲舒明确提出“君權天授”與“天人感應”,但在他之前早就有了此種觀念。
《尚書·泰誓》:“天佑下民, 作之君, 作之師, 惟其克相上帝, 寵綏四方”。
秦始皇命李斯在傳國玉玺上刻了“受命于天, 既壽永昌”。
由此可見, 至少在先秦就有了上天賦予人間帝王以正統政權的思潮,而這種理念也傳播至民間。
如此一來,天象變化對于君王來說就非常重要,那代表天意在改變。
各種天象被賦予了不同含義,區分成為吉兇兩大派。
為了掌握天象變動,對其觀測研究就變得非常重要。因此,天文學成了中國古代的重要學科,且設有特定部門管理。
我們比較熟悉的是明清時期的“欽天監”。
往前回溯,它有着不同名稱。宋元有司天監,隋唐叫太史局,秦漢有太常所,而在先秦此類官員稱之為太史。
在不同朝代的不同年代,其名稱或職能亦有所更改。
總體而言,随着朝代更疊,這一類官員的職位從最初位于核心部門漸漸變為身處清水衙門。
先秦時期,太史的地位很高,職能範圍很廣。
編寫史書、管理國家文獻、任命大臣、掌管祭祀、演算天文歷法等等,這些人似乎是無所不能。
秦漢改制,太史令的權力被極大縮減。主要任務是編寫史書與演算天文歷法。
等到了東漢,史書也不用編寫了。往後歷代基本只要搞一搞天文歷法相關研究。
天文官員的權力在縮小,并不意味着天文對于皇權的重要性減弱。
欽天監這個部門變得越發神秘,它所處理的事務被蓋上了機密标簽。
因為天象代表的吉兇變化會引起民心動蕩,而皇帝要确保觀天術不可為外人所用,以防引起天下動蕩。
《舊唐書》就有記載,給司天臺官員上了一層保密屬性。
大致說:司天臺負責占蔔吉兇是國家機密工作,近期聽說其中官吏多與朝廷其他官員以及番邦人往來。這不行,需要明令禁止,讓禦史臺随時查訪。②
此類命令不僅限于唐朝,比如明朝也有類似的。
《通志天文秘略》是明朝欽天監的天象占蔔專用書籍。
現存萬歷年的手抄本,而在開篇寫有洪武七年的序章。其中提到“此本只可傳靈臺,勿傳人間術家”。
天文知識是統治者的機密,民間不可得,而且一般官員也不可得。這樣才能确保天授君權的神秘性與正統性。
世間事多有兩面性,極少情況下能讓人獨享好處而絲毫不沾它帶來的負面影響。
古代皇帝也逃不出這個規律。
以天命所歸區別帝王們與芸芸衆生,帝王獲得特殊地位,也就逃不開天象變化所帶來的附加意義。
天降祥瑞固然好,但天總有不測風雲。
兇兆天象比好兆頭多,往往被聯系到上天對帝王與統治階層的不滿上,這就會引發朝局不穩。
比如彗星襲月、白虹貫日、太白經天等等,這些都是人間要發生災禍的征兆。
現在請聽題。
有一位帝王人年近半百,很有“福氣”地接連遭遇熒惑守心、星墜為石、石上刻有不祥字跡的奇異現象。
看視頻的諸位,把這位幸運兒的名字打在屏幕上。
哪怕不知道這段歷史,你們也能聯想到他是誰。小孩子坐的那一桌都知道了,誰家天下二世而亡?
讓我們脫口而出——秦始皇嬴政。】
水鏡前,嬴政面無表情,心中翻江倒海。
在死後被鮑魚覆屍足夠慘了,而他在死前居然還要遭受這一連串的重擊嗎?!真是死不瞑目了。
不過,今天沒有天崩地裂的覆滅感。
上個月,遭受了胡亥滅秦與趙高謀逆的沖擊,他的抗暴擊能力已經飛速提升。
影像開始時,咕咕說了超高天文知識能延年益壽。
換句話說,這些異常現象所代表的兇兆應該能被化解吧?只要懂得化解之道,就不會憤怒、狂暴、不安了。
另一個世界,朱元璋對着水鏡,表情有點古怪。
終是憋笑沒憋住,大笑出聲:“哈哈哈——”
行了,他不羨慕了。
咕咕偏心就偏心吧,長壽秘訣要用遭遇如此天象去換,他要不起。
水鏡:
【根據《史記》,嬴政死于始皇三十七年,而這些異象出現在他臨死前一年,那時嬴政是什麽樣的身體情況與精神狀态呢?
這就要從始皇二十八年說起了。
那時,嬴政四十周歲。
四十而不惑,這年他第二次出巡,遇上了術士徐福,命徐福出海找仙山。
在遇到徐福之前,嬴政有沒有尋仙求長生的想法?
個人以為是有的。
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,盡管秦不似楚重巫術,但不會堅定否決神仙的存在。
始皇帝一統六國,自诩受命于天。
不僅是向朝臣、黔首、敵對分子等宣告他有坐穩帝位的正統性,其本人也認同這種觀念。天子就是天命所歸,是特別的存在。
四十歲,以現代的标準還沒步入中年,但對于秦朝的大多數人而言已經到了大限将至時刻。
不去比百姓的低壽命,就比一比秦國以往的君王。太遠的也不看了,上數嬴政祖宗八代活了多久。
嬴異人三十五歲,嬴柱五十一歲,嬴稷七十四歲,嬴驷四十五歲,嬴渠梁四十三歲,嬴師隰六十二歲,嬴肅生年不詳,嬴昭生卒年月不詳。
在看了歷代秦國國君的年紀後,四十歲确實是會讓人産生年齡危機了。
嬴政所處那樣的時代,有着那樣的身份地位,想求長生且付之行動就不足為奇。
他不只任命徐福出海尋仙,在此之後陸續有方士三百多人抵達鹹陽。
其中出名的是盧生與侯生成了始皇身邊的紅人,為其占蔔吉兇,同時尋覓不老藥。
我們都知道以現代社會的醫學技術仍舊無法讓人達成不老美夢,秦朝時期何談找到不老之法。
然而,嬴政不知道!
他很重視這件事且一直在努力。到了始皇三十五年,也就是尋仙七年後,他沒有放棄而是更虔誠。
《史記》中寫了,為了成功修仙,他把很重要的自稱都改了。“吾慕真人,自謂‘真人’,不稱‘朕’。”
起因是盧生說的一段話。
想要尋仙,途中會遇上惡鬼阻攔。為避惡鬼,必須隐匿行蹤不被它幹擾。
如此一來才能遇上神靈真人。這種真人居住在雲端上,與天地同壽,而要問其求仙藥就要先見着面。
嬴政是皇帝,不可能徹底隐匿行蹤,但不處理政務時就會保密行蹤,而自稱真人就是為了距離神靈更近一些。
《史記》記載了一則案例,如果這種行蹤被人洩露會如何。
說是有一次,嬴政巡幸梁山宮,看到李斯的車騎路過,排場很大。
對此,嬴政私下表示很不高興,但沒對外臣說。很快,丞相卻減少了随行人數。
嬴政更加不悅,認為這種改變是有人悄悄傳給李斯知曉。
當即審問那天出行相關的所有近侍,沒有人招供,就将其全部處死了。
如果記錄完全屬實,近侍們全被處死,嬴政确實是殘酷,但歷代帝王也不遑多讓。
皇帝的話語豈能不經允許就輕易外傳。
今天透露皇帝私下說了什麽,明天透露其位置,說不定引來刺殺危機。
不過,這也側面反應出秦始皇四十七歲時的心理狀态。
如此處死一大批近侍,外臣會不知情嗎?必然是知情的。
嬴政毫無遮掩,他就是不寬和,就是要寧可錯殺也不放過。
問題轉回尋仙上。
以盧生為代表的方士來到鹹陽好幾年了,提出了各種我們現在聽起來離譜的尋仙求藥辦法與要求。
結果呢?
假的,終究是真不了。
方士們煉藥用什麽原材料?
多用五金八石三黃,具體內容根據流派不同而各異。
大概包括了金銀銅鐵錫,還有像是雌黃、雄黃、硫磺,以及朱砂、曾青、黃丹等等。
我列舉的這些原材料,用今天的詞彙簡單翻譯幾個,上過化學課的人多多少少知道它們的毒性。
雄黃,硫化砷;雌黃,三硫化二砷。朱砂,主含硫化汞;黃丹,別名紅鉛,又稱四氧化三鉛。
砷化物、水銀、鉛,吃了想要成仙,也是身體毀滅的那一種成仙。
後來,這些原料中的某些被用作不易察覺的暗殺武器,讓人慢性中毒而不可醫。
秦朝時期,方士清楚丹方有毒嗎?
絕大部分人應該不認為有毒。畢竟煉丹求長生的歷史之長,哪怕僅僅從秦朝開始算,也至少延續了兩千多年。
當時選擇這些原材料,或看重其稀有性,或将看重它的屬性與煉丹的五行理論能相互結合,而對毒性知之甚少。
據說,始皇帝手下的方士搞出了元水,一種含有水銀的藥劑,給死者試了試發現能保持屍體不爛。
四舍五入大法開啓,将它給活人用豈不是代表青春永駐。
那卻只是妄想。
時日一長,服用丹藥身體會給出不适反應。
嬴政在這方面也不會傻到底,那麽多錢投了下去,奇葩規矩也虔誠遵守了,永生不死的效果怎麽還不來?
騙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,就要把一群方士騙子給活埋了。
秦亡之後,此案越傳越歪。
在有心人的改編下,成了秦始皇坑殺儒生。
東漢以後一直流傳着很多人都聽說過的秦始皇殘暴坑儒之說。
嬴政求仙,半天長壽未得到,體內堆積亂七八糟毒素,還背了一口超級黑鍋兩千多年。
這仙給修的,不如當初做凡人。
吃好喝好,勞逸結合,心态放寬,說不定多活二十年,和他曾祖父一樣可以活到七十多歲。
不幸中的萬幸。嬴政死了,他不知道自己背鍋兩千餘年。
勉勉強強對始皇帝而言,這能算是一個好消息吧?】
水鏡前,嬴政臉色已如黑炭。
這算哪門子好消息。現在朕沒死!朕都知道了,蠢人竟是朕自己!
哪怕召見盧生等方士尚
未發生,可對史書上的始皇帝所經歷一切,他可以完全感同身受。
如果沒有出現水鏡,那些就是自己必定會做的事。求的是長生,卻親手毒殺了自己,太諷刺了。
就聽咕咕繼續:
【誅殺沒用的方士,發生在始皇三十五年。現在讓我們盡可能推測秦始皇彼時的身心狀态。
服丹藥多年,身體慢慢垮了。長生求不到,心情越來越糟。心情越糟會影響健康狀況變得越差,身體不複年輕而急求仙藥不得,心情更差。
死循環可不就來了。
正在這種時候,始皇三十六年,三大異象出現。
當時,從皇帝到黔首都相信天象與吉兇相關,而天空中出現了殺傷力最強的“熒惑守心”。
從馬王堆出土的《五星占》,漢代的天文占星著作。其中記錄了不少秦朝事,比如從嬴政登基到漢文帝三年的土木金三星位置。
它提到的熒惑守心時,如此說明:“(火)與心星遇,則缟素麻衣,在其南、在其北,皆為死亡。”
對于“熒惑守心”的解讀,這些話概括起來就一個字「死」。
非要多幾個字就是「超兇。天下或有戰亂起,死人死一片,或是皇帝本人死了。 」
為什麽會如此解讀呢?
這就要從古人對“熒惑”與“心”的不同看法說起。
熒惑,《呂氏春秋》對其釋義,是“熒熒火光,離離亂惑”。
這顆星看起來似一團火焰赤紅,而它的運行軌跡時正時逆,飄忽不定。
人們掌握不了它的軌跡,不安全感油然而生。
外加看到它血紅的顏色會聯系到血流成河,對這顆星也就喜歡不起來,随之給了它許多負面的意象。
以貌取人是通病,以貌取星亦然。
《史記》稱“熒惑星”是“殘、賊、疾、喪、饑、兵”的兇相。《荊州占》稱:“其行無常,司無道之國”。③
相對而言,「熒惑守心」中的“心”,在古人眼中的形象就大不相同了。
這裏的“心”,指是心宿二。
此前提到天上二十八星宿分屬東西南北四象。
心宿二,在東方蒼龍的第五宿。
心宿總共有三顆心,心宿一被認作“太子”,心宿三被認作“庶子”,而最亮的心宿二就是“帝星”。
它憑什麽呢?
理由不複雜。
心宿二非常明亮,運行軌跡規律,能幫助地上的人确定季節節氣。
比如耳熟能詳的“七月流火”,意味着夏去秋來,天氣轉涼。
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歷書《夏小正》,其中提到了心宿二。
“五月,初昏大火中。大火者,心也。心中,種黍、菽、糜時也。”
此處五月,當然不是現代公歷的月份,而是周歷五月。
心宿二在黃昏時出現在正東方,意味着春天到來,可以開始一年的種植。
這種天象給人帶來的感覺非常美好。
一年之計在于春,生機勃勃的日子開始了。民以食為天,春耕播種是最基礎的民生要事。
因此,心宿二也被認作是農神、龍神的化身,後來慢慢演變為帝星。
細心的觀衆一定注意到了古籍裏記載時,也叫它“火”、“大火”。
不錯,古代人歡喜地稱呼它為“大火”星。
此火星非彼火星,不是我們所熟知太陽系八大行星之一的火星。
心宿二,其實非常遙遠是天蠍座α。對比地球在銀河系邊緣,它靠近銀河系中心。
如今廣為認知的火星,在古代把它叫做什麽呢?
答案剛剛已經出現了。
不錯,就是那麽諷刺,它是人們不喜歡的熒惑星。
從現代的視角回望過去,兩顆火星在中國古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命運。
一顆被奉為帝君,一顆則淪為災星。人類根據觀測到的表象,賦予了它們天壤之別的含義。
眼下,再看「熒惑守心」,它指的是災星闖入了帝星領域。
試問怎麽可能不天下大亂。輕則兵禍,重則帝亡。這種預兆,百姓信,皇帝也信。
始皇三十六年,嬴政看到了這個天象。
這位帝王的身體與心理本就極其不健康。
大兇之兆,哪怕不至于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,也是極其可怕的當頭一棒,帶來非常沉重的精神壓力。
假如嬴政有超前的天文知識呢?
那就沒有這一連串的問題。
熒惑守心,只是一種單純的天文現象。
首先,熒惑星就不是災星。
古人最不理解的是它的飄忽不定,為什麽看起來一會正行一會逆行呢?因為火星與地球繞太陽運行軌道不同所導致的。】
水鏡畫面切到了簡易的三星兩圓圈示意圖。
中間是金色球太陽,第一個圓圈是藍色地球公轉軌道,其外側的是第二個圓圈紅色火星公轉軌道。
兩個圓形狀不一樣。地球的是接近正圓的橢圓,而火星的是橢圓。
一段簡易的拟态轉動視頻開始了。
【我們都知道地球與火星繞太陽轉。因為公轉周期與速度不同,站在地球上觀察火星時,人的視覺效果會看到火星逆行。
這裏不放公式了,不讓大家被死去的物理知識攻擊。
簡單說來,火星逆行的出現頻率可以被估算,大約兩年一次,一次維持兩個多月。
古人不知道這種天文原理,而未知令人恐懼。火星被扣了災星帽子,何其無辜。
如果嬴政知道了熒惑星的運行規律,他還會認為這是災難象征嗎?
不是災難就不必擔憂恐懼,更不會精神壓力極大。懂得這些知識的人還會一門心思找方士煉丹服用嗎?不吃丹藥,不懼異象,身體倍棒,吃嘛嘛香。】
水鏡前。
嬴政:目瞪口呆!
朱元璋:呆若木雞!
現在是對熒惑守心不恐懼了,但他們腳踩的地居然圍繞着天上的太陽在轉圈圈嗎?
騙人的,怎麽可能呢!不,朕不信!
作者有話說:
PS晚上六點二更~
——
①參考《一文帶你回顧中國人的太空征程史》中國科學技術館
②《舊唐書》開成五年(840年)十二月:
“司天臺占候災祥,理宜秘密。如聞近日監司官吏及所由等,多與朝官并雜色人交游,既乖慎守,須明制約。自今以後,監司官吏不得更與朝官及諸色人等交通往來,委禦史臺察訪。”
③《荊州占》東漢時劉叡所作,現已逸失,多散見于《史記》《漢書》《後漢書》注釋及《開元占經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