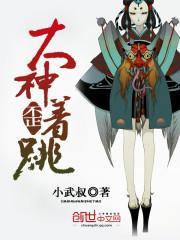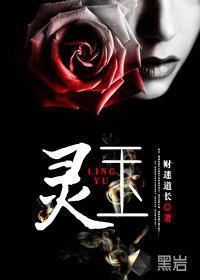8 所謂的一家人
雨後沒兩日,楊志同吳掌櫃請了三日假回來幫忙張羅宴客之事。他進城多年,又能說會道,添了他這個幫手,楊家衆人都覺得輕松很多。
這一日早晨,楊志帶了足夠的銀錢,喊了村裏幾個自小交好的玩伴後生幫忙,又借了裏正家裏的驢車進城采買,不過午時就押着滿滿一車吃用之物回來了,而楊家要大辦百日祭酒席的消息也在村裏傳開。
其實大夥平日都在一個山溝裏過日子,誰家窮富也瞞不過別人。
陳氏在世的時候,楊家省吃儉用的供楊誠讀書,也算上等人家,可是陳氏過世後,楊柳兒跟着病倒,請醫問藥把家底都刮光了,村人心裏早就把他們一家降到末等,就是有那還記得陳氏百日祭的人家,也以為楊家能預備幾碗臊子面應付一下就成了,沒想到楊家卻是要大操大辦。
有些婦人好奇,就打着幫忙切菜的名頭上門走動,結果一見到院角的柿子樹下挂着整羊,案板上還有一條條的五花肉、一盆盆的小銀魚、泡發的幹蘑菇、大塊的火腿以及油紙包着的燒雞,人人都驚得瞪圓了眼睛,轉而口水忍不住滴答落下,盤算着明日一定要早早上門,不為了別的,能混上兩頓吃食就頂得上半年油水了。
楊家沒有女主人,楊杏兒這大閨女就硬着頭皮接待這些上門的嬸子伯娘。不必說,又被拉着閑話好久,當然主題只有一個——楊家到底在哪裏發了大財,不然怎麽有銀子采買這些好吃食?
楊家上下對于這樣的探問,早就商量好了應對之策。不論衆人怎麽問,楊杏兒就是一句,“大哥攢了多年的工錢,就為給娘親一個體面的祭日。”
衆人裏有聰明的,雖然一百個不相信,但也沒有厚着臉皮繼續問。也有人琢磨楊柳兒年紀小,想從她嘴裏問些真話,可惜楊柳兒一臉懵懂,被問得急了就嚷頭疼,吓得衆人不敢再開口。
不說衆人如何揣了一肚子的好奇幫忙拾掇食材,只說隔日的百日祭。
楊杏兒和楊柳兒剛過子時就爬了起來,雖說今日家裏請了方圓幾十裏最好的廚子掌勺,但送到墳頭供奉娘親的飯菜,她們姊妹卻決定自己動手。一來是身為子女的孝心,二來也是告慰死去的娘親,盡管放心投胎去,她們已經有能力照料好父兄。
姊妹倆一直忙到天亮,總共做了四道菜,一道木耳炒肉、一道幹菜扣肉,一道豆腐盒子加一道辣子雞塊,剛剛裝進食盒,負責酒席的劉大師傅就帶着兩個徒弟,趕着兩輛騾車到了,騾車上不但有鍋碗瓢盆,還有方桌條凳。
幾個早就守在院門口的後生一聲吆喝就幫忙往下卸東西,楊志聞聲從窯洞裏跑出來,當先遞了個白紙封給劉大師傅。
這叫進門錢,其實也是一半的工錢,另外一半要等酒席散掉,主家再付,若是主家滿意,還會有額外的賞錢。
劉大師傅不動聲色的掂了掂,随即臉上就帶了笑,待一進院子見到食材就更歡喜了。他們掌勺這一行最怕的就是吝啬的主家,買二斤肉偏偏讓你整出一桌豐盛的席面,若是達不到就到處宣揚廚子手藝不好,簡直氣死人,但顯然楊家不是那樣的人家。
羊肉、豬肉、火腿、燒雞,稱得上豐盛之極,若是這樣還整不出好菜,他可就真該被罵了。
很快的,楊家院牆裏外都搭起了臨時竈臺,大徒弟砸了羊骨開始熬湯,小徒弟則搬起大盆和面、揉面,忙得跟陀螺一樣。
Advertisement
劉大師傅正動手炸魚、炸肉丸,院子裏漸漸盈滿濃郁的香氣,再随着山風散出去,整個村裏的鼻涕娃子們好似心裏長了草,顧不得老娘打罵,瘋跑到楊家門外。
楊家大門前豎起了高高的木杆子,長長的紙錢串在風裏晃晃悠悠,陳家兩兄弟扶着老娘,帶着妻子孩子趕來的時候,遠遠看到都紅了眼眶。
今日燒了紙錢,陳氏在人間最後的念想就要斷了,以後投胎轉世就不知要去哪裏了。
陳老太太更是哭得眼淚直掉,嗚咽着,“蕙娘啊,你怎麽就走了,娘疼啊。”
陳家兩個兒媳趕緊勸慰,“娘,你可不能哭啊。否則妹子走的不安心,錯過了好人家怎麽辦?”
正這時候,剛剛走到院門口迎客的楊山和楊誠也快步走到跟前,爺倆兒一起行禮,陳老太太趕緊擦了眼淚,一大家子人進了院子。
老話裏規定,百日祭要趁着太陽沒出來的時候進行,否則逝者的魂魄不敢出來享用供奉吃食,自然也不能最後看家人一眼。
見外祖母和舅母們趕來,楊杏兒放了心,匆匆同楊柳兒換了新縫的素色衣裙,然後出了門。
楊山親手拔出院門前的木杆子,交由楊志舉着,一路往陳氏的墳頭去了。楊誠撒着紙錢,楊柳兒姊妹則挎着食盒跟在後邊,村裏幾個平日同陳氏交好的大娘也跟在後邊,一邊低聲說着陳氏的好處一邊嘆着氣。
很快就到了墳茔地,擺上供菜,燒了紙錢,楊志帶着弟妹磕頭,最後又把陳氏的舊衣燒了一件,就算斷了陳氏在陽間所有的念想,至此澈底陰陽兩隔。
楊柳兒發了會呆,又從食盒裏拿了幾個和面的饅頭撒在墳頭不遠處的空地,算是供養附近的游魂孤鬼,省得他們在地下欺負陳氏。
幾個大娘看得都是點頭不已,直道陳氏沒有白疼這個小女兒。
一番忙完,太陽也已經越出光禿禿的東山梁。楊家人雖然不舍,但家裏還有衆多賓客等着應酬,只得一步一回頭的回去了。
山腳下終于回複了寧靜,但是沒過一會,樹叢裏就響起窸窸窣窣的聲音。只見一只紅毛小狐貍偷偷探出小腦袋,許是見沒有什麽危險就樂颠颠的跑去陳氏的墳前,在供菜前嗅了又嗅,末了才對着那盤幹菜扣肉大快朵頤,可惜,它還沒吃幾口就被一個少年拎着頸子提了起來。
“你這個饞嘴狐貍,平日又不是沒給你帶吃食,怎麽又跑來吃這些供食?你也不怕被鬼魂抓閻王殿去。”
小狐貍掙紮了半晌也不見少年松手,于是惱得扭頭就要咬,少年這才終于放它下地,見它依舊對那盤扣肉情有獨鐘,好奇之下就拈起一塊紅通通的雞肉扔進嘴裏。
雞肉還帶着微微餘溫,辣得他差點跳起來,但咂咂嘴巴卻覺得滋味十足,少年猶豫了一下,到底也坐了下來大嚼一番。
一人一狐貍就這樣吃了個飽足,最後倒在草叢上曬太陽,少年想起方才那個一身月白衣裙的小丫頭,低低嘆道:“怪不得她跑去街上賣什麽汽水,原來也是沒了娘……”
山風從少年臉上吹過,好奇他眼裏為何有些同病相憐的意味,但沒容它多琢磨,少年就閉了眼,山野間再一次陷入了寧靜……
楊家院子裏這會已聚滿了人,村裏成了家的爺兒們幾乎有一個算一個,都到齊了,就是婆娘也帶着小娃們蹲在院牆下,一邊閑話一邊兒曬太陽。
見楊家人一進院子,衆人就趕緊站起來,紛紛開口寒暄,楊山帶着兩個兒子一路同衆人見禮,楊柳兒姊妹則去了竈間接替陳家人。
雖說陳家是外家,但今日也是客,院子裏早就替他們留了一張空桌,陳家兩個舅母還怕楊柳兒姊妹張羅不過來,想要留下幫忙,但見楊杏兒手腳麻利的裝着點心盤子,楊柳兒也開
始分茶葉倒熱水,她們也就退了出去。
很快的,十幾個後生肩膀上搭着白布巾,手裏端着紅漆托盤聚到了竈間門外。
姊妹倆通力合作,每個托盤上都放了一盤四色點心、一壺熱茶,後生們笑嘻嘻的端着送去各張桌子,楊家的謝客酒席就開始了。
農家人節儉,只有到了年節之時,老人們的櫃子裏才能裝進幾斤粗點心。楊家既然決定大辦酒席,就沒有吝啬的打算,點心盤子裏放了馬蹄酥、炸油糕、驢打滾和小籠肉包,樣樣都是量足又美味,衆人嘴裏互相客套着,手下卻是沒有客套,茶水都顧不得喝上一口就塞了滿口點心。
院子外邊的婆娘和淘氣娃子們眼巴巴看着,卻也沒有進院子,哪怕是家裏再潑辣的婆娘,再受寵的孩子,這時候也不能上席面,否則就要被人家指着說沒規矩,但他們也不是多心急,畢竟劉大師傅的小徒弟,已經把切好理順的面條端了出來,一挂一挂的放在大簸籮裏,只等大鍋裏的水開了,煮好澆上肉臊子,他們就能解饞了。
待點心和茶水撤下去,後生們正要上涼菜的時候,楊家院子外又有人趕到了,呼啦啦的連老帶少足有十幾人。有熟悉的村人見了,臉上已是露出不屑之意,原因無他,來人正是楊家老宅一夥。
楊山同兩個兒子對視一眼,都有些無奈又氣惱。
這樣的日子,按理說作為自家人,他們應該前一日就來幫忙,即便不來幫忙,今日也該早早趕過來,但他們偏偏幹活的時候躲懶,吃飯的時候也遲到。
遠遠的還在楊家門外,楊田一見院子裏的模樣就有些臉紅,大步走到楊山跟前小聲說道:“三哥,阿娘昨日趕着我去砍柴,早起賣去城裏……”
可楊田話還沒說完,楊山就拍拍他的肩膀,示意他不必多說。
這會楊家老少已經走到了跟前,楊老頭還沒開口,顴骨凸出、斜眼高鼻,生來一副刻薄相的楊老太太卻是搶了先,劈頭蓋臉的罵道:“老三,你還認不認我和你阿爹了?我們沒來,居然就開席面了,你媳婦死了,老娘還沒死,誰給你的膽子?”
而一旁尖嘴猴腮,下巴還長了一撮黑毛的楊老大掃了一眼桌子上散落的點心渣子,後悔得腸子都要青了。心裏埋怨道,早知道就不聽老娘的了,什麽給三弟一家沒臉,以後更好拿捏,到底錯過了用點心吧。
這麽想着他不耐煩的插嘴,“娘,你就別唠叨了,趕緊坐下吃飯吧。”
“吃吃吃,你就知道吃!”楊老太太剛抖起威風,沒想到大兒子第一個拆臺,氣得伸手就要打人。
楊老大卻是一個閃身坐了下來,半點不在意的催促着,“是不是要上涼盤了?趕了一早上的路,我早就餓了。”
都說不是一家人,不進一家門。他的媳婦朱氏還有光棍兒子也都麻利的坐了下來,直等着開飯。
身形矮胖的楊老二不知在哪裏找了錦緞褂子穿在身上,可下邊卻配了件黑色的夾棉褲,樣子不倫不類的很是滑稽,偏偏他還覺得自己很體面,高人一等,昂着下巴在各個席面掃了一圈。
末了不知想到了什麽,楊老二眼珠一轉就笑着打圓場,“娘,三弟許是忙的忘了。咱們都是一家人,別計較這些,三弟過後給娘賠罪就是了。”說着話,他擡腳在兩個侄兒的屁股上踹了一腳,罵道:“這裏哪有你們的位置,還不去後竈幫忙。”
兩個侄兒不情不願的站了起來,楊老二扯着老娘、老爹坐了下來。至于楊老頭則一直紅着臉,顯然還是個知道羞臊的,但他多年來在家裏就沒有說話的權力,這會除了低着頭,就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楊老二的媳婦錢氏,見桌面上沒了她和孩子的位置,就撇撇嘴也去了竈間。
而從頭到尾,楊山父子三個一句話都沒說,臉色黑得吓人。
家裏之所以大操大辦,就是為了給故去的陳氏做臉面,活着時候沒有享福,死了之後怎麽也要風光一把,多少算是一個補償。但是楊家老宅衆人,偏偏在他們端出來的臉面上狠狠糊了一團爛泥,恐怕自此月餘,村裏人茶餘飯後的閑話就離不開自家的這點爛事了。
但事情已經如此,這酒席還得繼續。楊志一揮手,示意劉大師傅趕緊上涼盤,後生們又魚貫而出,每桌又上了四個涼盤,和一壇最烈的燒刀子。
楊山端起酒碗,勉強說了幾句謝言,末了一口灌了下去,衆人随後也幹了酒碗,酒席這才正式開始。
有酒有菜,院子裏很快就恢複剛才的熱鬧氣氛,好似楊家老宅的衆人不曾出言刁難一樣。
楊杏兒和楊柳兒在竈間裏隐約聽到幾句,雖然不真切,但掃一眼父親和兄長的臉色就知道大概了。再看兩個厚着臉皮讨要白布巾的堂兄,還有伸手抓點心吃的伯娘,姊妹倆真是氣不打一處來。
楊杏兒開口就要發飙,倒是楊柳兒攔了她,還是那句老話,家醜不可外揚。今日鬧厲害了,到底還是他們一家子丢人,怎麽都要把酒席熱鬧圓過去,之後再同他們好好說道一二。
劉大師傅也是個有眼色的,很快又喊着後生們上了熱菜。
五花肉燒豆腐、蘑菇溜肉片、炸丸子、蔥爆羊肉,各個都是香噴噴、熱呼呼,吃得衆人都是贊不絕口。
院外的婆娘娃子們這會也端着陶碗吃上臊子面,到處都是吸面條和湯水的聲音,楊家老宅衆人更是手下筷子翻飛,楊老大不時還高喊後生們添菜,可惜衆人都裝作沒有聽到。
擺在院角的大鍋,裏頭的羊湯這會已經熬得奶白,撒上些鹹芫荽的碎末,就是壓軸的起席湯了。此時衆人都已吃了七八分飽,舀上一碗羊湯,再掰了一張面餅泡進去,通通填進肚子裏,撐得連走路都有困難。
楊家父子站在門口送客,一衆村人吃了頓好飯,又看了半場好戲,都帶着笑臉走了。
席面告了段落,劉大師傅和兩個徒弟又開始煎炒烹炸,準備了兩桌酒席,喂飽自己和忙碌半晌的後生們。
陳家人除了陳老太太帶着兩個小孫子坐在屋檐下,其餘陳大舅和陳二舅夫婦加上楊田都開始幫忙拾掇殘席,雖然菜盤子和饅頭筐都是幹幹淨淨的,可碗盤桌椅也得擦抹。
柳樹溝用水有限定,不過規矩也不死板,逢年過節或者誰家有個紅白喜事也能随便用。
楊田挑着擔子,走得飛快,大桶的清水倒進陶盆裏,陳家舅母就挽起袖子開始洗刷,楊柳兒姊妹要幫忙都被攆到一旁。
反觀楊老大、楊老二兩個,連同幾個堂兄又厚着臉皮擠到酒桌上,哪怕打着飽嗝,手裏的筷子依舊沒有停下。
大伯母王氏和二伯母錢氏兩個則抄着袖子在院裏院外轉悠,大有挖地三尺,甚至把楊家所有值錢物事都印在眼睛裏帶走的架勢。
楊柳兒看得氣悶,實在不喜她們的模樣,伸手扯了扯姊姊的袖子,楊杏兒會意,悄悄轉身回了竈間,把剩下的火腿和臘羊肉、各色幹貨以及炸丸子炸魚,但凡不帶湯水的都藏了起來。
果然,王氏和錢氏蹓跶回來,開口便是讨要“剩菜”,楊杏兒聽見了,爽快的端出半盆羊湯,可裏面除了幾塊豆腐,連個肉片都沒有。
王氏和錢氏當下就冷了臉,正開口想罵的時候,楊誠卻走了進來。
對于這個讀過聖賢書的侄兒,妯娌倆還是有些忌憚的,小聲嘀咕了兩句就端着盆走了,出門時順手又牽了兩只陶碗,美其名是半路渴了好舀點湯喝。
好不容易最後兩桌席面也撤掉,劉大師傅帶着兩個徒弟收拾好,東西裝好車就要回去了,楊志把另外一半工錢付了,另外又給了一串錢打賞,打點的師徒三個樂颠颠走了,一衆後生也都紅着臉、帶着一身酒氣告辭了。
陳家衆人瞧了瞧楊老大幾個,有些擔心妹婿和外甥外甥女吃虧,但他們畢竟姓陳,相處再親近也不好攔着楊家人,最後還是離開了,臨別前,陳老太太拉着楊柳兒的手,囑咐她過些日子一定要去老林河住幾日。
楊柳兒依稀記得外祖母以前很疼愛“她”,自然多了幾分親近,笑嘻嘻地應了,又抱着外祖母的胳膊送出院門老遠,惹得陳老太太又紅了眼眶。
而楊老太太見院子裏沒了外人,下巴又擡高了三分,呼喝着倒水拿點心。可惜楊柳兒和楊杏兒都到躲竈間去了,裝作沒聽見,她氣得想開口再罵兩個孫子,楊老頭卻是一聲不吭,起身就走了。
楊老太太沒有辦法,又嚷着要楊山一收了麥子,就趕緊把養老糧食送過去,這才不情不願的出了院子。楊田更是幹脆,扯着同樣不願挪步的楊老大和楊老二,腳下生風一樣的走遠了。
好不容易等到楊家人走遠,楊杏兒飛跑去關了院門,回頭見父親和兄妹看過來,她紅了臉,小聲道,“我是怕老鼠進來。”
楊山沉默良久,長嘆一聲回了窯洞。
楊柳兒好奇,琢磨了半晌,自覺從兩個兄長那裏打聽不着什麽底細,于是就借口拾掇吃食,偷偷拉着姊姊閑話。
楊杏兒也是氣惱祖母一家不着調,開口就把她知道的瑣事都說了一遍。
原來楊家先前日子還算不錯,楊老大和楊老二都讀過幾日書,奈何沒有天分又不勤懇,最後都回家種地了,輪到楊山,雖然聰明又想讀書,但楊老太太卻偏心能說會道的楊老大、楊老二,放着他們到處游蕩不管,硬是留着三兒子在家做農活,讓楊山不到十二歲就成了家裏的主要勞力。
後來楊老大、楊老二成親,輪到他的時候,楊家的家底被楊老大、楊老二敗壞了大半,楊老太太舍不得聘禮,就想随便找個身體有殘疾的閨女,想着許是不用花銀錢就能把人娶回來。
好在有句話叫姻緣天定,楊山一次出門進城時碰巧救了扭腳不能走路的陳氏,兩人互有好感,最終結成了姻緣。但楊老太太許是覺得三兒子沒有按照她定好的道路走下去,心存不滿,陳氏進門後就使勁刁難,甚至懷了頭胎也被折磨得流掉了。
陳家兩兄弟知道後直接帶人打上門,要替妹妹撐腰,最後是楊山主動要求分家,帶着妻子淨身出戶,每年給老宅一百斤麥子,算是盡孝的養老糧食。
楊山也是個有骨氣的,不想被人家說依靠岳家讨生活,出了老宅直接落腳在楊家和陳家中間的柳樹溝,勤勤懇懇的在土裏刨食,倒也養活了一家人,且這麽多年來,不管年頭好壞,豐收還是絕産,從來沒給老宅少過一粒麥子。
楊老太太逢人就罵三兒子夫妻不孝,可楊山家這幾個孩子從出生開始,別說衣衫,連塊點心都沒從她那裏得到過。
楊山一開始還會帶妻兒回老宅拜年,後來見茶水都喝不上,也就歇了心思,每次自己走一趟,稍坐一會盡到禮數就罷了。
楊柳兒聽了半晌,這才明白今日外祖家衆人為何同楊家人連個招呼都沒打,原來早在多年前就撕破臉了,不過說起來,這些都是陳芝麻爛谷子的事,同她也沒有什麽關系,但只看
楊家老宅衆人今日的吃相和行事,她就半點興不起親近之意。
思及此,她不由在心裏告誡自己,以後還是盡量遠着吧,他們不惹事就好,若是犯到自家,她也不會念什麽血脈親情。